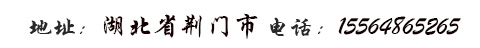时间丧失在海洋中
|
时间丧失在海洋中 兔草 在他生活的地方,既没有沙漠,也没有海洋。人们借由虚构抵达远方,他们建造价格不菲的海水浴场,运来大批量的沙,用蓝色的水填充干涸的眼。 他第一次意识到不对劲是在七岁生日时,那一年的九月,他被母亲带入海洋馆,通过巨大的透明玻璃与一只会飞的鲨鱼对视。“鸟为什么会出现在海里?”他向母亲发问,得来的答案并不令人欣慰,他的母亲摸着他的头说,“这不重要,我们是来看海豚和企鹅的,别的鱼不重要。” 在回家的路上,他继续追着母亲发问,问题更加古怪,包括“企鹅为什么不在南极而在水族馆里”“蛇为什么住在一个玻璃缸内”“鲨鱼为什么没有吃掉身边的人”……他的母亲摸着他的头,不知如何回答,年轻的母亲想,要是这孩子能缩小到婴儿期就好了,那就只用想尽一切办法哄他睡觉——喂奶、讲故事、哼儿歌、冲奶粉,都可以,总好过编造谎言来解释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根本不是用来解释的。 在回家的车上,他伴着车身的摇晃坠入梦乡。梦里,他置身于无垠的大海之中,在他眼前,那只展开双臂滑翔的鱼正越飘越近,就在他以为自己即将从鲨鱼血腥的嘴里打捞到终极真相时,彩色的泡沫忽然将他推得很远,他一头撞到了珊瑚礁上,等他醒来时,眼前的一切都消失了,现实又极不留情地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蝙蝠?” “你说什么?” 他突然意识到那不是鲨鱼,也不是鸟,只是一种形似蝙蝠的奇异生物,在下一站,他不顾母亲的阻拦,决然地跳下车,冲向一间书店,他在书架间来回翻找,终于找到一本介绍海洋生物的书,在书的第页,他终于再次撞见那个困扰他的生物——蝠鲼?他抬起头问:“妈,这怎么念?” “fupen?” 少年很快意识到母亲对这个词语的犹疑,也就是说她压根也不认识这种动物,所以无法解释“鸟为什么会出现在海里”。他笑了笑,忽然觉得一切就像闹剧一样。也就是自那时起,他渐渐明白这城市里大多数人并没有主动选择什么,而是受到广告路牌、电视剧、传单、软文等的诱惑,在百无聊赖之际,将自己安放进某座建筑物里——商场也好,电影院也罢,海洋馆也可,这些场所并没有任何不同,他们只想看到时间花在看起来有用的地方。 他第二次意识到不对劲是在九岁那年的暑假,奶奶牵着他的手走进商场一隅的儿童乐园,巨大的塑料滑梯如瀑布倾泻,小孩子们黑色的头颅在伪造的海洋里起起伏伏,欢声笑语连成一片,他的奶奶指着那片海域说:“去玩吧。”他站在塑料制作的海洋球边,双脚如圆规似的两边画圈,同时搜索词语来表达内心的不愿意。“你这个孩子怎么总是跟别人不一样?”他撇撇嘴:“我想去真的海里游泳……”奶奶一把抱起孙儿往乐园中送:“什么真的假的,你没玩过怎么知道不好玩?你看别人多开心,就你哭丧着脸。” 他脱掉鞋,慢慢朝充斥着海洋球的乐园里滑下去,活像一个去海里寻死的自杀者,海洋球渐渐没过他的脚背、膝盖,他回头朝“陆地”看去,他的奶奶正在和另一个年纪相仿的老奶奶大声议论什么,嘈杂的声音淹没所有对话,但他仅凭唇形就能辨认出奶奶正在说他的坏话,就在那一刻,他打算将自己藏起来,藏在任意一个角落,千万不要被家人找到,打定这个主意后他便四处勘察地形,在仅两个小时的游玩时间中,他耗尽心力寻找躲避之处,可每一次转移阵地总能感到背后有一双眼睛虎视眈眈地监视着他。 是谁?是谁呢? 为了把自己塞进好不容易寻觅到的视觉盲区,他将身体蜷曲起来,可尚未发育好的幼小身体经不起如此折腾,好几局对战下来,他还是没有藏进滑滑梯背后的洞穴里,就在他筋疲力尽之时,身后响起重重的声音:“小伟,你往哪里钻啊?” 他被奶奶一把抓起,如同被捕捞的幼崽。他并不知道一个年近六旬的妇人为何有这般力气,“奶奶,奶奶,我只是想看一下里头有什么。”这解释近乎玩笑,他再一次在人生的控制权上败下阵来,而得胜者也没有得意忘形,奶奶在这个位置上已经待得够久了。 “我再玩一会儿,就一会儿!” “好吧,那你别到处乱跑了,就待在这里别动了。” 他在蓝色的海洋球中躺了下来,感到光滑的圆形塑料正在摩擦他的身体,他忽然什么也不想做,时间在这一刻静止,睡神再度俘获了他。在梦中,世界只有一种蓝,从天到海再到屋顶,甚至人类皮肤与牙齿的颜色,竟然都是一种颜色,他因此分不出自己与旁人的差别,仿佛有一道海啸,拍向人间,所有人都变成了水分子。海洋是蓝色的,人工海是蓝色的,海洋球是蓝色的,这之间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只要我们认为是一样的,就是一样的。 这一次的清醒没有那么容易,他起先嗅到了一股咸腥的味道,这让他误以为自己还在那个海蓝色的梦里,可当他缓缓睁开眼后,发现自己躺在饭桌边,脸上尽是菜汤与菜叶子,通过模糊的光影,他看到父母正在争吵,吵架的内容无非围绕他展开。 “我就说让你怀孕的时候别乱吃感冒药,现在好了吧?” “孩子又不是我一个人的,再说当时都五个月了,五个月怎么打?” 他的父母推断他为生育失败的瑕疵产品,但目前已经恢复不了出厂设置,只能任其发展,他们想象不到少年的未来是什么,少年没有未来,他们也就没有未来,这对年轻的父母并不想看到这个局面。 “我没病。我只是太累了。”醒来后,他将责任推诿在课业过重上,并主动向父母认错,以后会少看漫画,早点睡觉。 “医院看看吧,有病治病,没病更好。” 第二天,医院,经过详细的检查与问诊后,医生笑眯眯地对前来看病的一家人说道:“我觉得这个孩子没什么毛病,有毛病的是你们,没事总觉得孩子这里那里有问题,我看他挺好的,你们不要神经过敏。” 他的父母相视一笑,眼中有遮不住的喜悦,这喜悦撺掇泪花溢出,让他鼻子发酸,他感动的不是父母对他的关心和体贴,而是他的事情终于以看似正当的方式沉冤得雪。 父亲、母亲、医生的“调查”已经结束,而他对自己的调查才刚刚开始,为了让整件事隐秘地进行下去,他找了许多借口,离开家,一个人独处,在父母眼里,他变成了一个常去图书馆,常去足球场的好孩子,只有他自己知道,在无数个阳光灿烂的白天,他是如何趴在桌上,倒在草坪上,沉沉睡去。 他总是以跑的方式经过各类交通工具,在地铁和公交和轮渡上突然睡觉不是什么好事,再说,他也不是每一次都能坐上座位,如果突然倒下去,结局只有一个——医院,如此一来,一切都将暴露。待在图书馆的第三个月零三天里,他终于在一堆医学书籍里搜索到了一个名词——发作性睡病。 他在那张写有“发作性睡病”的纸上反复摩挲,好像这样就能与地球上其他微乎其微的病者达到交流似的,其后的许多年,他将孤独视为可耻的词语,大多数人总是滥用了这个词,他们根本不知道真正的孤独是什么。 他第三次意识到不对劲是在十四岁那年的暑假,他在奶奶遍植月季的阳台上寻到了一株濒临死亡的玫瑰,花朵在接受大剂量的灌溉后会逐渐失去生命活力,直至枯萎,他也差不多,从医生将他从母亲的子宫剥离出来那一刻起,他就成了一个不断注水的容器,他累了,他需要睡一会儿。醒来时,太阳西沉,墙上时针指向傍晚六点,才睡了两个小时不到嘛,还不赖,他准备起来去看一场球赛,可手脚动弹不得,他陷在一个柔软的床里,所有人都用焦灼的目光试探他。 “你已经睡了三天三夜了。”睡了这么久吗?他疑心这是谎话,人不可能睡这么久,两抹白色的影子穿过灰色的人群来到他的面前,一个是医生,一个是护士。医护人员的权威身份宣告了整件事的真实性,他没有反驳权。 后来他索性开始随时随地、不分场合地睡觉,有时是在亲戚的酒席上,在众人举杯的刹那,他如自由落体,笔直地坠下去,发出呼呼的鼾声,这行为像一击响亮的耳光,拍打在他父亲脆弱的脸颊上,“你儿子怎么了?”每当有人发出这样的疑惑时,他那个工作狂父亲总这样解释:“太累了,孩子学习累。” 后来他渐渐从这病中寻出了一丝好来,好几次他醒来后还继续假寐,在那个时间段里,他听到父母小声议论着一些事,诸如作业怎么办,钢琴班怎么办,学习成绩怎么办之类的,如果是醒着的时候,他必然要起来与父母对峙,而现在他只需要躺着就好了,考试的时候躺着,吃饭的时候躺着,做作业的时候躺着,他可以以此为借口逃避生而为人的种种责任。 他们开始逐渐放弃他,“他们”指的是所有的亲戚,包括父亲、母亲、爷爷、外婆等,他们甚至谋划换一个培养皿,但现实情况不允许,他的母亲在家庭会议上声泪俱下地说:“我已经绝经三个月了。”活了快一个世纪的爷爷发出结案成词——“实在不想养了,就把他赶出去,他自己能活下去的。” 他在墙壁后偷听到了这一切,但心下并不生气,他们终于打算放弃他了,或者修饰得更好听一点,主动放弃对他的控制,他喜上眉梢,那意味着他即将迎来自由的日子。在那一年夏天来临时,他拾掇好了行囊,与父母辞行,表面的说法是他打算去一间医院工作,实际上,他只是想逃出父母空造的五指山而已。 医院吗?家人问。 医院,医院的名字叫“白日梦”。 这当然是一种谎言,但其余人也不见得说了真话,通过多年的精心推演,他已经掌握了构筑谎言的基础知识,首先你需要一个证明,他拿出一张A4大的文件纸,上面写着猩红的大字——“通知书”,他的家人交头接耳,试图用毕生的经验来解释这张纸的存在。 “医院。”他的父亲从事了一辈子的校对工作,总是试图在纸上寻到蛛丝马迹,破获什么旁人未曾知晓的大案,然而,并没有,他一生都被堵塞在错字错句构筑的窄道之上,甚至养成了一些吹毛求疵的毛病。 “要不让他去儿童乐园工作吧,那里工作轻松,人际关系简单,虽然工资不高。”他的母亲小声表达着意见,这孩子毕竟在她的子宫里住了十个月,哪怕只是房东与租客的关系,她也不忍心直接将他推到熙熙攘攘的大街上,在怀孕期间的噩梦里,她常梦到洪水、地震、车祸,这种不祥感伴随整个孕期直至孩子出身,她趴在丈夫早已弯曲的肩膀上哭泣:“我就知道是这么个结果。” “在儿童乐园能做什么呢?那都是废物去的地方。”他的父亲一贯声音洪亮,每吐出一个字都恨不能切断一条钢管。在承受了高频的讨伐后,他感到疲乏。远处,泡泡从洗衣机管道里漏了出来,逐渐爬向蔚蓝色的墙壁。他看到童年在上升,逐渐增大,最后受到空气的挤压与折磨,碎成一些带有肥皂气味的水珠。 “行吧,那也可以。”他主动结束了这场争吵,同时将伪造的入职通知书撕毁,“什么时候去呢?”他问母亲,“我说什么时候去儿童乐园上班?” “下个星期?下下个星期?你总要给我一点时间吧,”母亲面色为难,“要不这两个星期你先休息休息,海水浴场刚开放了,你去玩玩呗?” 他从母亲手里接过一张全市旅游年票,这张票是一张简单的通行证,可以在全市八十个景点自由来往,售价为两百元,但大部分购买了年票的人都没有去过任何一个景点,最多的也就去了十来个,他们只是伪造出自己热爱出行的假象。 第二天清晨,他穿越整座城市,在经过那片细幼白沙的海水浴场时,他感到困意袭来,海水浴场距离他的家不过千米距离,只要他的父亲站在27层的高楼朝这边眺望,仍能看到他,哪怕他看起来只是一个蚂蚁大的黑色斑点…… 在清醒与酣眠之间,并没有一个白日梦来过渡,他睡得快,醒得也快。醒来时,他感到鼻腔与嘴里堵满了异物,那是沙粒倒灌的感觉,他看到小铲子在身边飞舞,那个看起来不过六七岁的孩子正在为他制作坟墓,没有人问他醒了没,何时醒的,为什么沉睡,那孩子只是全神贯注地建立沙堡,他举起手,握住孩子手里的铲子,“停一下。”他说:“可以不把我的头埋住吗?我需要呼吸。” 大约在八岁时,他的母亲常带他来海水浴场,他也喜欢玩沙子,沙子可塑性极强,可以瞬间聚沙成形,也可以瞬间摧毁,这种游戏天生适合喜怒不定的小孩,那时的他也喜欢和同伴玩用沙子埋人的游戏,直到有一天被大人明令禁止——“不准再躺在沙子里面,不然就回去罚站。”他那时并不知道这是一种流传在民间毫无依据的忌讳,譬如他的母亲还说,不准把筷子插在装满米饭的碗里,她说你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吗?那意味着这碗饭是给死人吃的,筷子看起来像两柱香。所以他也不能躺在沙堆里,尽管那种感觉如浮在一个装满温水的浴缸中,“那是给死人躺的地方啊……” “叔叔,你再睡一会儿吧?”那孩子突然开口说话,吓了他一跳,他起初以为他是哑巴,“我不能睡了,我睡了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醒。”“没关系啊,我可以叫你起来。”他摸了摸孩子的头,终于全身浮出沙面,“我还有别的事, 我必须走了。” 他离开了那片沙滩,但并没有走多远,他打算在海里待一会儿,或者直接走到海的正中心去,等待蓝色的水没过脚掌,没过膝盖,没过脖子,没过头顶……他把手机拿出来,准备放进包里,塞进储物柜,就在那刻,电话突然响了起来——“喂?”“喂喂喂。” 一段急促的命令扑头盖脸砍出来——“我已经给你找好了工作,但是你明天就得来上班。”他笑了笑,重新穿好衣裳,将蓝色紧身的游泳裤穿在里头,仿佛随时要下水游泳一样。 在回家的路上,他经过了那个第二天要去上班的儿童乐园,用小学生作文里的话来说,简直是欢乐的海洋,在巨大的海洋球娱乐设施面前,他感到自己就像第一次走进海洋馆里的小学生,一切都是陌生的,一切都是新鲜的,他打算进去躺一会儿,就一会儿。 可他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他不能通过正常的渠道走进那片蓝白相间的海洋,于是他绕道,从扶梯的后头偷偷溜进了一个盲区,他走进那片海,用蓝色、白色的球覆盖周身,然后轻柔地躺下来,就像躺在一片白沙之间。“在相对论中并没有一个唯一的绝对时间,相反地,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时间测度,这依赖于他在何处并如何运动。” 他躺在海洋球之间,一动不动,好像再度睡着了般,在他身后,招牌上写着硕大的字——“海洋球撞地球”。他猜想地球很快就会毁灭,毁灭在他脑内坑坑洼洼的星球表面,时间丧失在了海洋球里,飘向宇宙至深处。 注释: ①发作性睡病:年在法国召开了第一次发作性睡病国际研讨会,会上对该病作了如下定义:这是一种病因不清的综合征,其特点是伴有异常的睡眠倾向,包括白天过度嗜睡,夜间睡眠不安和病理性REM睡眠。 (完) 文/兔草图/可矣工作室视觉组 编辑/帅朋江 赞赏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hthaituna.com/htbhjb/1324.html
- 上一篇文章: 大堡礁上油污垃圾触目惊心30年已消失
- 下一篇文章: 江门发挥三大优势谋划蓝色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