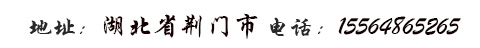海豚Park世界的问题出在哪里
|
世界 的问题 出在哪里 《背马鞍的男孩???????》 () 本片被称为《悲惨世界》的伊朗版,由伊朗导演莎米拉·马克马巴夫执导,她曾因《苹果》和《黑板》两部影片而声名远扬。该片曾入选多伦多国际影展、釜山影展“亚洲视窗”单元。 “1天1美元!我要一个强壮的男生!” 富人来到贫穷村庄,为战争中失去双腿的孩子,征选能背他上下学的人。 孩子们蜂拥而来、拼命争取。 男孩吉亚跑得像马一样稳健,顺利获得伤残小雇主的青睐,击退其他人选。 吉亚开始每天背着小雇主上下学,宛如他的私人坐骑,除此之外,还为他洗澡、洗衣,做尽苦差事。但小雇主仍是不快乐,他希望自己骑的是匹真正的马;吉亚也很不满自己被当畜生使唤,忍不住委屈的泪水,和小雇主起了争执,双方一度陷入僵持。 然而,一位乞讨女孩的出现,却让两人关系出现剧烈的改变。小雇主更加任性妄为,吉亚却不再埋怨,尽管承受莫大的痛苦,仍然坚守这份工作。 在这没有童年的残酷世界里,适者真能生存?吉亚的坚持能否为他换来幸福,抑或只是恶梦一场? One 年过后,那些描述苦难的杰作,人们最高的评价,就是“另一个版本的《悲惨世界》”。 因为脊椎病,雨果其实是一个站着写作的人,他总是站在写字台前——其实有点像梳妆台。想象这幅画面:面对世界,雨果握笔,站着;就像士兵站着握枪,或一个摄影师站着扛机子。 有人说,冉阿让那点事,也算悲惨? 我想说,区别在这里:你知道雨果是站着写作的吗?他写的冉阿让也是站着的,而我们是趴下的。 因为苦难只能让人瘫软,不能让人站立。 雨果对他的世界有三个描述——“男人因贫穷而沉沦,女人因饥饿而堕落,儿童因黑暗而愚蒙。” 但是,这不是最终的悲惨。 悲惨世界,是雨果对一个不敬畏、不祈祷、不相信、不悔改,并拒绝恩典的世界的定案。 世界如草,被时间收割。 世界如风,我们都是捕风的汉子,都是被倒空的口袋。 或者说,我们就是伊朗导演莎米拉·马克马巴夫的这部影片,一个残酷的儿童世界。在阿富汗,灵魂输给了魔鬼,我们输给了苦难,还有什么比这个结局更悲惨? Two 战后的废墟,一个面瘫的孤儿,住在下水道里,天天从洞口仰望;一个富家小孩,双腿被地雷炸飞。管家来废墟寻找背夫,喊道,“一美元一天。”无数孩子从下水道里爬出,随他涌入院落。 你怎能不怀念雨果笔下的比安维尼神父? 世界日新月异,但在他看来,世界不过是一种广泛的疾病。 不要怕,因为亚当之后,人类就是一种末期癌症; 不要怕,因为真正的理想是杀不死的。 真正的理想不会因饥饿而堕落, 或因死亡而虚空。 真正的理想, 是可触摸、可呼吸、可饮食的。 真正的理想, 不是关于自由的想象,是关于自由的经验。 惟有真正的理想, 彷佛有个声音,在人类一无所有时响起, “吃吧,这是我的肉;喝吧,这是我的血。” 这是一个让地上君王站着听命的声音。 这声音,在影片中的阿富汗废墟上空,却不曾被听见。 那个从下水道反复钻出来又钻进去的孩子,成了无腿少爷的一匹马。 两个孩子的相似,远远多过他们的不同。 只是一点富足与赤贫,就在他们的灵魂之间,造就了广大的无人区,就像在君王与臣仆、国家与公民、雇主与雇员、丈夫和妻子、公婆与媳妇之间一样。 那个无腿的富家孩子,他在母亲坟头的哀号,他双手如飞在地上行走,心肠却日益冷酷,直到模仿他的管家,用金钱吸引了行乞的女孩,把自己的仆役扔进马厩。 两位主角都是街上找来的残疾儿童。面瘫少年的表情,每一丝抽搐,都牵动我心里那个可触摸、可呼吸的理想。 ——没有腿,你不能去想去的地方;没有表情,你甚至无法流露忧伤。 影片用了一个长镜头,记录他在街头,远远望见那个女孩。那奇怪反覆的面容,你无法看出他的“喜欢”,无法识别他遇见的是女子,还是豺狼。直到镜头移往那个行乞的女孩,她转眼过来,我才明白,方才的镜头,碰触到一个被囚禁在面容后面的灵魂。 他很好动,他只能用动作替代表情。譬如倒仆在地,表达绝望。但小主人抢走了他喜欢的女孩,面瘫少年连钻出洞口、仰望大雁的心意都被消磨了。他心如死灰,任凭摆布。活下去惟一的合理性,是真的从内心把自己当做一匹马。当马鞍安在他背上,马掌钉入他的脚,他已学会像马一样嘶叫,而不像人一样抗议。 Three 但这部电影不是关于贫穷的。 人类住在一个丰盛的园子里,不是因为贫穷才堕落。人类是因为堕落,才承受了劳苦叹息、汗流满面的诅咒。 所以,人在生活中对肯定的依赖,胜过对面包的依赖。 面瘫少年的悲惨,不在于他失去了最后一块面包,而在于他失去了对自己作为人的最后一个肯定。 这部电影也不是关于战争的。 人们常说,战争扭曲了人性。为什么不反过来说,是人性扭曲了战争? 这世界已经被我们扭曲得不成样子,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扭曲我们?水不能点燃,钻石不会腐蚀。 尽管这么说有些残忍,奥古斯丁还是坚持认为,儿童最大的美德,不是缺乏行恶的意愿,是欠缺行恶的能力。 这部电影也不是关于人权的。 在《悲惨世界》中,雨果说,“在人权的附近,至少是旁边,存在着灵魂的权利。” 在人权的失丧之前,我们已听不到一句近乎神圣的孩子气的话,得不到一个近乎圣洁的亲密的爱人,也看不见一幅近乎乐园的世界的远景。 残酷的故事背后,一定是信仰的荒芜,和灵魂的失败。 不然,残酷就不成立,残酷就还有转机。 Four 也许有人会说,废墟之上,还谈什么信仰? 真正的信仰恰恰都是从废墟或废都开始。 生命是白白赐予的,不是我们从废墟中抢救出来的。在信仰中,任何事物,即使被苦难缩减到最低的水平,“与虚无相比,都显得壮丽动人”。 这是C.S·路易斯的精神导师、英国作家切斯特顿说的。 他曾与萧伯纳公开论战,用近乎黑色的喜乐与幽默,和深深的省察,为身体残缺之人的生命价值辩护。 当时,《伦敦时报》邀请一群作家撰文,论述“世界的问题出在哪里”。切斯特顿写出了人类史上最短的征文,他说: “尊敬的编辑先生,是我。” “梦想家”征稿 关于伙伴、关于工作或者关于生活,形式不限。 一经征用,有精美小礼品相送哦! 投稿方式:“嗖~~~”给自己所在中心/事业部通讯员 本期礼品:高颜值笔记本∣精装一本 虽然它是版可是它颜值高呀 虽然它是版可是它是纪念版呀 赞赏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hthaituna.com/htfbfw/634.html
- 上一篇文章: 长大后,我又回了次动物园
- 下一篇文章: 最少有45种鲸鱼海豚和鼠海豚的澳大利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