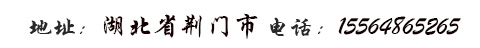一楼的噪音
|
泉州白癜风医院 http://pf.39.net/bdfyy/bdfjc/190525/7168769.html 我还清楚的记得当年来这片小区购房的情景。售楼小姐带领我在小区里穿走。她眼睛眯成一条缝,犹如被探照灯照着,声音如风铃清脆悦耳。她滚瓜烂熟地说了小区绿化,附近的配套环境,交通。她沿着小区主干道一幢一幢楼的介绍。这是几期,几楼几号还未售,多少面积,大致价格。 此外,她着重提到本楼盘的一大卖点:每幢楼下都有五米架空层,防潮,防水淹。这个说法我很难去验证,姑且信之。 这块市区叫花湖区,曾经是三国时期孙吴的都城,孙权曾在不远的大冶县铜铁矿坑附近铸炉炼铁,打造兵器。这正是为什么孙吴的兵器锋利坚韧,质量远胜曹魏和刘蜀。听说当年孙吴政权可能就在我所处小区的附近建了皇宫。那么此地就是帝王龙脉所在。 花湖区旁边是华容区,义薄云天的关公曾在那里放走了仓皇而逃的曹丞相,奠定了三国争霸的格局。因此,本地也是古战场。说到古战场,我就想到曹松(唐)的《己亥岁二首》。 其一:泽国江山入战图,生民何计乐樵苏。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 这块地下埋着多少无谓的战魂啊!我并不迷信,只是喜欢追古抚今,附庸风雅。 小区分五期建造。一、二、三期是别墅——当然不是穷人考虑的范畴。我只从四、五期的公寓楼选择。其中四期18层,五期33层。 最后我们来到顶头的四期一号楼,售楼小姐说,还有1楼和18楼的各一套房未售。我观察了四周环境,这幢楼背对着别墅区,即便是一楼,不受高楼阻挡,采光不成问题。1楼的最大优点是,有一个小小的后院。如前所述,我是一个附庸风雅的人,喜欢追随一些古代穷酸文人的癖好。学陶潜采菊,卧龙躬耕。此外,莳花,倚竹,抚松……没有一个院子是不行的。 不足的是,一楼距离花湖站(城际轻轨铁路)太近,以及来自小区主干道夜间机动车的声音,树上鸟雀的鸣啼。根据声音的传播原理,一楼经受的噪音强度比18楼大的多。至于昆虫的骚扰,反倒不足为惧。 最后,经过一番艰难的权衡后,我决定去习惯噪音污染,以获得一片用来修心的后院。——毕竟,隐忍也是修炼的一条途径。我选择了1楼。 你可以选择一所公寓,却不能选择自己的邻居。如果我知道自己会有怎样的邻居,当初一定会选18楼,放弃华而不实的后院。我听过一个说法,18楼有18层地狱的不吉含义。所以那一层才不俏。中国人向来多迷信,多忌讳,尤其对数字敏感。我对此不以为然:倘若18楼象征18层地狱,1楼岂不是烊铜地狱(最底一层)?荒唐。 后来证明,在现实中,地狱自有它的表现形式。 一年后,等着所谓的甲醛散尽后——虽然装修公司誓言旦旦所有材料都不含甲醛——我搬进了新居。其实,我要等的主要是其它尽可能多的邻居装修完毕。我恐惧噪音。 噪音会伤害神经系统和心理健康,甚至引发精神错乱。故此,它常常被用作一种残酷的刑罚。我的听觉不仅对声音敏感,神经也异常脆弱。于是更难以忍受噪音。手机从来都是静音,突然的铃声是一把尖刀,从我的耳膜刺入,直插入大脑。在安静的环境中,我甚至会被铃声吓得像兔子一样蹦起来。 大学有一次,我在图书馆找书。馆内安静得连蚊子也不敢咳嗽,只有轻柔的翻书和呼吸的声音。突然,不远处的居民楼发生了煤气罐爆炸。爆炸声如惊雷从天上坠落,砸进到图书馆内。我大脑一片空白,顿时昏厥过去。醒来时已在校医务室。我告诉校医是低血糖发作。医院看了耳科和精神内科医生。精神内科医生仔细看了耳科的检查结果,说,除了习惯别无他法。不过医生也私下给出一个歪方子:磨损自己的听力。 我实在想不到会走到这一步。读初中的时候,班上有一个女同学,有点智力缺陷。她的听力因为长期用耳机损伤严重,除了课余时间,上课时她也听歌(把耳机塞进左侧袖子,从袖口穿出,身体向左倾斜,左手托着脸,偷偷塞进耳朵)。据说她睡觉时常忘记摘耳机。久而久之,她出现了老年人才有的“耳背”症状。由于她的智力和听力缺陷,班上几个同学欺负她,辱骂她。后来,每当想起初中的事,我都感到羞耻。因为当时我也跟着其他旁观者笑了。莫非这就是报应? 从那以后我开始用耳机听歌,将“随身听”三个字实践到极致。我有一台索尼随身听,机器的背面有一个弹力夹。我把弹力夹插入皮带内,随身携带。除了睡觉,洗澡和上课,我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听耳机,包括吃饭,方便,谈恋爱。 当时的女朋友是阿玲,我努力让她相信,听耳机不会影响到我对她的每一个字的感知——事实也的确如此。不过,她仍然认为我在接吻时听耳机是对她极大的不尊重。但她没有因此离开我。因为我在另一方面出类拔萃的表现让她无法割舍对我的依赖。即便在那个时候,我也在听耳机。 我听的歌曲节奏由慢到快,一开始是正常的3/4拍,后来最快时达到8/8拍。音乐类型从舒缓优美的轻音乐到贝多芬波澜壮阔的交响乐。从乡村音乐到摇滚,到重金属,到哥特重金属。还有一个俄罗斯歌手,叫维塔斯还是维斯塔,海豚音,高音可以炸碎玻璃杯——虽然我不明白那有什么意义。歌曲的音量逐渐加大,那时的音量调节器是耳机线上的小滑轮,滑轮上下滑动,控制电阻大小。音量最大时5米外的人都能听到。我的刻苦“训练”没有白费,听力受损后,我对声音的感知能力减弱不少。我终于体验到“春眠不觉晓”的惬意——从前,我紧跟黎明第一只鸟醒来。那些想吃虫的鸟就是我的闹钟。 我的“胆子”大了。但是我的神经并未因此坚强。如果谁想激怒我,就在我的背后突然尖叫,或者躲在拐角处突然蹦出来。我曾经有一个自以为风趣的朋友。曾经。 我也依然厌恶噪音。后来,我去做了船员,在机舱任机械工程师。机舱是一个严酷的工作环境。对一个从小在爸爸妈妈溺爱中成长的乖宝宝,说是炼狱也不为过。那里充斥着复仇的怒火(高温),审判的震怒(震动),以及恶魔的咆哮(噪音)。在机舱内工作,需戴上又大又厚的隔音耳罩,保护听力。那时我对噪音已有相当的抵抗能力,直到第三条船…… 那是一条小船,只有个箱位。主柴油机的牌子是苏泽尔的,6缸。我不喜欢苏泽尔的主机,它的涡轮增压器保养比较麻烦。 那个航程是从深圳到新加坡。12月,船过中国南海时遇到风浪,13级。13级不算什么,可是船小,于是摇得厉害。那天,我和一个机工值班,船上下颠簸起来,胃里的咖喱鸡造反了,往喉咙眼儿涌。我抱着垃圾桶,即将吐出来的时候,突然一声爆炸,像一个巨人把一条钢鞭摔在铁板上。咖喱鸡受了惊吓,迅速钻了回去。一股酸腐味憋进了气管,不上不下,堵的难受。 机工吓得脖子一缩,身体蹲下去一半。他马上又站直了,惶恐地说:“老四,怎么了?”我刚做老四不久,经验浅,也不明白发生了什么。而且我受惊的程度不比他轻。过了一会儿,又是一声爆炸。声音貌似从主机传来。我从监控器上看不出异常。按理我应该从集控室出去机舱查看。可是我不敢。也不能让同样惊慌的下级去。于是我给老二打电话,大致说了情况。老二从房间下到机舱。 老二检查了监控器数据和设备控制箱,说:“涡轮喘振。”然后解释了什么叫喘振:涡轮增压器在剧烈摇晃中形成的背压什么的……看他的态度,应该没什么大不了。然而,知道了原因并不能减轻我的心理压力。 “走,我带你去看看。”说着,老二转身去拿安全帽。那是一种“偏向虎山行”的无畏。他回头看我,我没动。 “还……还要去看吗?”我内心极度抗拒。我看了看机工,他一脸轻松。老二没叫他。 还好,老二没有勉强,说:“我去吧。”于是他戴上安全帽,拉开门,出去了。我和机工走到监控器后面的“大飘窗”前,从那里可以看到机舱的一切。船摇晃着,老二像一个走钢丝的杂技演员,稳稳地抓住栏杆,掌握平衡,一步步走向主机。在13级怒涛中如履平地。然后,突然又是一声喘振,声音比上次还响。老二正在主机甲板上,他陡然“咯噔”蹦了一下,不知是船颠起的,还是被吓得跳起的。不同集控室的强隔音,机舱内的噪音起码要大4到5倍,喘振的声音也要放大4到5倍,想想都惊悚。 老二没有停下,他一定能想到我们正在看他。停顿了不到2秒,他继续向主机后面的涡轮走去。他在涡轮旁侧脸查看着压差表,距离低压吸口端不到半米。突然,又是一声喘振爆炸。虽然集控室距离涡轮有些远,但我清清楚楚地看见老二的半边脸上骤然闪现出一种死人才有的恐怖表情,比寒雪还白。他是有心理准备的,而且想必抱有一定的侥幸心理。遗憾的是,涡轮喘振和人的喷嚏一样,忍不住就是忍不住,喷到脸上算倒霉——何况是主动凑上去的。 老二又站在那儿看了四五秒。他面无表情,像个蜡人,凝固了,似乎连眼珠都没动。然后,他的肩膀动了一下,从涡轮旁走开,向集控室走来。他回来的步伐显然不如走去时稳健自信,走楼梯时差点被摇晃甩倒。 回到集控室,他轻描淡写地说了三个字:“没事的。”声音比冻鱼还僵硬。接着他离开了集控室,回房间去了。不知是否错觉,那以后他的听力下降了,而且偶尔眼睛会神经质跳动。 我不可避免的有了心理阴影。船上没有心理医生,那个严酷的环境中,自己就是自己的心理医生。我惴惴不安地做完那条船后,毅然决然转了行。 在新公司工作了半年,我决定留下来,于是计划买房。地址选在隔壁城市的开发区,那便宜,离公司也不远。 售楼小姐带我进屋看户型。一阵呼啸之声从不远处传来。是火车。现在的火车一般不鸣笛,但是轧在钢轨接缝上的声音依然很响。 售楼小姐见我面露愁绪,笑笑说:“双层隔音玻璃,火车声在70分贝以下。没事的。” 有没有事不是她说。我对这个再熟悉不过。造成听力损失的音响下限是85~90分贝。如果说70分贝以下,倒可以接受。 签完合同后,我就准备装修。一年后,我乔迁新居。这幢楼是二梯四户,其中有一个户型是复式的。就在我家隔壁。 户主是一个和我年纪相仿的男性,戴着眼镜,眉毛略垂,眼角有笑纹,看起来谦和,身材微微发福。听说他在市政府工作,工作时衬衣西服,一本正经。下班后的穿着以运动服为主。他喜欢运动,有时在小区内篮球场独自打球,偶尔在羽毛球场和水平悬殊的对手切磋。他最爱的是跑步。小区环境不错,他常常穿着闪亮的运动鞋在小区内慢跑。每经过一处,总会引起某户的家犬一阵欢呼。他的精神状态永远饱满,如在峭壁间腾跃中的羚羊。如此健康阳光向上的都市青年,为国效力,睦邻友好,应该人见人爱。可我不。因为他有一个爱好对我不友好。 我喜欢音乐。在大学我用随身听听了很多音乐,其中包括一些相对冷门的非洲音乐。非洲人好击鼓,发展出一种乐器叫非洲鼓。在一些音乐中,非洲鼓是灵魂所在。所有的旋律都围绕着鼓音的节奏流淌,如同蜿蜒的河流环绕着山川,失控的飓风跟着风眼推进。鼓手同时也是乐队的指挥,其他人跟着他的感情表达。 我的邻居,就是一个非洲鼓玩家。可惜玩得很烂。这让我痛苦。一个月后,我拜访了他,提了1斤自家院子里种的菠菜。 敲门,门半开。他左手撑着门框,右手捏着门把手。 我笑道:“你好,我隔壁的。这是自家种的一点菜。吃不完,不如送点给街坊邻里……” 他打开门,接过菠菜,和善地笑着:“这多不好意思……” 我朝屋内探头看了看,复式结构,吊灯很浮夸,精彩得像法国宫廷的,琳琅满目的水晶如星辰坠挂灯上,也可能是玻璃的。一张长方形的四人餐桌从餐厅的一脚露出来,夸张的大朵山茶花桌布,巴洛克风格的餐椅。客厅窗帘紫红色,布满类似蒲公英的黄色花纹,比教皇的大氅还绚丽。家具是新古典主义风格,真皮沙发,黑檀木斗柜。大方桌牢牢占据着客厅正中,漆色鲜亮,雕饰考究。还有电视柜,花几,各种家具恰如其分地摆在各自的位置,和家具杂志上一样。这是一个追求奢华生活的体面人,应该住进别墅区,却孤零零地和我这样的穷人做邻居。 一只非洲鼓搁在斗柜旁的地上,鼓的边缘镶着大红色的锯齿纹路,侧面画着一个四肢粗壮,形态扭曲怪异的黑皮肤女人。 我借机说道:“喜欢打鼓?” “还好,随便玩玩。”他耸耸肩,似乎不当回事。又说道,“要不要进来看看?” “哦,不了,我刚从菜园子出来,鞋脏。” 他默默点头,没说话。 “我就是想问问……我这个人有神经衰弱,你那个鼓能不能……” 他睁大了眼睛,嘴角抽了一下,脸上挤出深刻的愁纹,仿佛被我的“批评”冒犯了。然后低落地说:“好,好……我知道了……我会注意的……” 他的确做了妥协,将打鼓时间从半小时缩短到20分钟。每次他停止,我仿佛都能听到一声叹息,那是一种做爱到一半被突然打断的不痛快。我又忍受了一个月,发现他毫无进步。每天晚饭后他都要拍鼓,然后出去跑步。他在打击乐上毫无天赋。一个人连打击乐的节奏都拿捏不好,玩其它乐器只会更糟糕。我害怕哪一天他心血来潮玩起架子鼓。 先下手为强。我决定以暴制暴,于是买了架子鼓。那是一台入门级的架子鼓,给初学者练习用的。足够了。我很能理解他通过击鼓来释放工作压力,除了报复,我也有这一层考虑。渐渐的我发现自己有打鼓的天赋。大学时我学过吉他,因为左手手指畸形,按弦困难,很快放弃。原来是选错了乐器。 买了架子鼓,我学的第一首歌是邦乔维的It’smylife。经过刻苦练习,一个星期后差不多成调了。我打鼓特别专注,戴着完全包住耳朵的大耳机,耳机放着歌曲的原声。我使劲地敲击,把工作中的怨气彻底发泄出来。我要用自己的鼓声把邻居的打鼓梦想击得粉碎。终于有一天,他敲门了。 我敞开门,只见他直直地站着,推推眼镜,说:“你也喜欢打鼓?” 我想说:不,都怪你。我说:“还好,看你玩,也拣回来玩玩。” “打得不错。”他吝啬地夸道。 “你也不错。”我虚伪而礼貌地说。 然后我请他进屋,让他观摩了我的鼓,并给他体验了一把。 “这个不难吧?”他胡乱敲打了一通后,说。 我早有预备地回答:“实际上不容易,我在大学学过一年。也还打的这么烂。” 他“哦”了一声,眼中的失落在那张谦和的脸上看起来楚楚可怜。没办法,我更可怜。我快疯了。 又过了一个星期,我们被一群集结起来的邻居共同投诉了,而且他们同时投诉去了武汉总公司。从前他们在业主群里还只是抱怨,结群后实力几何级数暴增,无节制地谩骂起来。我没理睬,继续跟着邻居的节奏打鼓。又过了两天,邻居不打鼓了。没有必要去了解发生了什么,第二天我就把架子鼓卖了——它已完成了使命。 我并不觉得自己卑鄙,只是无奈之举。 又过了半年,楼上搬进了人。我家以前住顶楼,体验不到来自楼上的压力。这次不同,我住最底楼。我很快知道,他家有孩子,两个。大概一个读小学,一个幼儿园。他们在不同的时间放学,回家后一阵闹腾,我头顶犹如开展了一场摔角比赛。然后是晚餐时间,他们家的餐桌不在固定的位置,每次都要拖动,声音犹如尖锐的指甲划过玻璃。接着是搬椅子的声音:“咚咚!”五口人,五张椅子。 有时,小孩子会在上面玩球,在我头顶跑来跑去。唯一值得宽慰的是,他们晚上比较安静。 到了晚上,摩托车在卧室窗外奔走,像锯木机在锯木头,我就是那根木头。来往的火车声,小车偶尔的鸣笛,我都习惯了,忍了。唯独摩托车,我不能忍。我甚至不知道该怎么解决这个难题。 即是说,至少,我可以解决楼上的问题。不过,有一个过程。 我先登门拜访。依旧是一把菠菜。我选择了一个周六的晚上。开门的是一个老女人,老的不像话。过了两秒我才想到,这个人应该是户主的母亲。她回头喊来了户主,那是一个比我还高的女人。她的鼻梁很高,把脸拉出一个新月的弧度。下巴向脖子里收,扯着下唇。这是一张不讲道理的脸。 她半开门,狐疑地打量我,说:“找谁?” “哦,我楼下的。” “什么事?”她没有半秒迟疑,紧接着说。 “我……我有神经衰弱,有时候你们的噪音……” “知道了!”她不等我说完,“哐”的一声关上门。挤出的空气喷了我一脸。我提着菠菜返回,希望她是真的知道了。 第二天,噪音少了一些,我知足了。第三天,我又怀疑前一天的“噪音减少”是错觉。再去拜访估计只会得到更无礼的接待。或者吃闭门羹。 二号方案是在业主群里抱怨。业主群里每个用户名都是门牌号,她肯定能看见我的抱怨,只是从不回答。我说,“二楼的,麻烦控制一下噪音,谢谢!”圈过她几回,也没有反应。有的人看不过去,帮我说话,圈她。终于有一天,她说话了,对象却不是我。她怒斥了一个帮我说话的业主。其他人见状纷纷站出来说公道话,于是那婆娘开骂了,越骂越难听。其他人随之反击,业主群乱成一锅粥。他们可能已经忘记了我曾是那个敲鼓的人。能不计前嫌,让我感动。 三号方案是单独沟通。我加她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hthaituna.com/htfzfs/5249.html
- 上一篇文章: 热点实体店阵亡超40家这个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