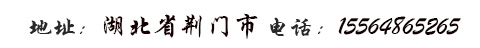麻风病人有传染性的可耻身体
|
青年谈·谈青年 在这个略显严肃的栏目里,我们会收集和罗列些许JIA工作营开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或当今公益活动遭遇的困境,抑或是青年志愿者发展中的瓶颈等等。篇幅所限,见识也有所不足,并不能详尽铺开描述或深入讨论,仅仅期望能引起身为JIA志愿者的我们有共鸣、重视、警醒、反思。 我们也会分享公益伙伴、学者关于青年人成长的文章,希望JIA的志愿者在这个时代背景下,有更多对青年自身定位的思考。 新冠病毒肺炎出现之后,在国内曾经一度被称为武汉肺炎。而疫情蔓延到全球之后,新冠病毒也一度被部分人称呼为中国病毒。也许某些称呼有着早期的不确定性,也许某些标签带着恶意的人种区分。感染疾病不是病人的错误,而压迫病人和污名疾病的人群却从未减少。 今天分享香港中文大学历史学讲座教授梁其姿所著书籍《麻风——一种疾病的医疗社会史》的节选章节“有传染性的可耻身体”。不论是鼠疫、麻风病、还是新冠肺炎,历史总是一次又一次的重演。 《麻风——一种疾病的医疗社会史》 有传染性的可耻身体 从19世纪中期开始,中国麻风病人象征了中国种族的两个“缺陷”:体质差、其疾病有传染性。关于中国麻风病的种族主义话语不完全建立在西方医学理论或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基础上,明清中国对麻风病的流行病学观点毫无疑问也支撑了此种话语。至少始于16世纪,麻风被重新定义为南方烟瘴地面的地方病。南方人,据说和文明中心的汉族人的身体类型不同,被认为更容易罹患和传染麻风病。与此同时,人们把麻风看作性交传播,传染性极强,主要影响纵欲或虚弱身体的疾病,对它越来越害怕。 书内插图 麻风病在病人身上循序渐进的发展,尤其是可怖的外部症状,以及关于其神秘的传播渠道的种种说法,使得麻风病成为个人以及集体的堕落、污染和道德缺陷的最流行、最持久的隐喻之一。在工业革命和帝国主义时代,和麻风病有关的旧隐喻现代世界的语境下边的意味深长。其中一种观点是麻风和麻风病人代表和体现了种族退化,这一点在19、20世纪之交仍未揭开麻风病的奥秘时更加如此。 例如,关于麻风病的传播问题,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洲医学界众说纷纭,遗传和传染是其中两个主要的假说,不过二者似乎互不相容。但是,不同的麻风病传播理论背后都有个共同观点,即某些种族特别容易得麻风病,尤其是炎热国度肤色较深的劣等人种。此观点和此时风行于欧洲的退化说相一致。那些认为麻风病是遗传病的人,尤其相信麻风病与人种有关。在某种程度上,相信麻风病仅局限于体质易得此疾病的有色人种,让白种西方人觉得宽慰。 在汉森发现麻风杆菌之前,欧洲出现了两位主要的医学报告,它们认为麻风病本质上是遗传的,绝对不是传染性的:其中一份来自伦敦的皇家医师学会“麻风病本质上是体质问题,它反映了恶病质或者整个系统的败坏情况。” 第一个来华工作的英国新教医学传教士合信,主要在年代把西方医学介绍到了中国。年,他指出麻风病是一个“特殊的、与体制有关的遗传性疾病,为炎热的国家所特有”。他没有“严格地认为它是传染病,单纯通过接触传染,但是它毫无疑问是个遗传病”。更确切的说,它是“影响中国人、印度人、回教徒、非洲人和其他居住在热带或热带附近地区人民的热带病”。年,麦雅谷和弗利斯医生注意到“麻风病在有色人种中的发生比在白色人种中更频繁”。 麻风病也被看做是处于文明的某个阶段的人种所特有。英国热带医学之父万生在年出版《热带疾病》之前,在中国南方做了大量的田野调查。书中他把麻风病列为热带病之一,不仅如此,它也是半开化的疾病:“野蛮人被豁免了,高度文明的人也被豁免了,但是当野蛮人开始穿衣蔽体,过定居生活,他就沦于麻风病之手了。”在汉口工作的希拉医生认为“血液呈病态”,受“某些疟疾肆行地区的不洁空气”影响的人会得麻风。换言之,他们认为麻风病侵袭那些居住在瘴气弥漫、被“野蛮”的生活和生产方式污染的环境中,具有某种遗传体质的种族。显而易见,中国人被认为是这些主要居住在瘴疟地区,退化的、半开化的种族之一,无怪乎麻风病会在中国流行。 书内插图 西方传教士和中医一致认为,麻风病盛行于烟瘴地区。早期的一些传教士,完全接受中国人的观念,认为此疾病除所谓岭南地区的闽广和其他南方省份之外,罕有。后来,就算发现中国的其他地区亦有麻风病后,瘴气致病说仍没有被放弃,而是为了切合论点进行了修正。甚至是在山东这样的北方省份,瘴气依然被认为是麻风病传播的原因。传教士艾约瑟引用其同僚亨特医生的观察报告说,“很可能如今发现麻风病的地方两千多年以来一直都有麻风,那样的话,这个病的存在肯定于遗传有很大关系。”然后他继续推测,“很可能中国的气候变得比古时候干燥寒冷,结果现在麻风病的发展不同于孔夫子时期,它好像被越来越干燥的气候赶到南方了。”19世纪末的中国,瘴气论被用作无限上纲的解释,持论者认为,既然中国的许多地方都发现了麻风病,包括北方,那么这些地方肯定有瘴气的,中国总的来说肯定是个瘴气弥漫的热带国家。 麻风病是生活在烟瘴地区的特定的劣等人种的遗传病的这个观点,本应让中国人觉得不快,但讽刺的是,它却和明清时代,甚至延续到民国时期的中国传统麻风病观点如出一辙。年3月,国民政府卫生部向省政府下达命令:“查吾国癞病发生初仅及于两广,续传于闽浙,渐入长江流域,而更有蔓延黄河以北之势。其为害之深,与其传播之广,实为疾病之尤。”调查令的目的是敦促各省开展全面调查,尤其是调查现有的麻风病院。实在发人深省的是,至年,中国的政治精英依然相信这样的论调,即麻风病起源于最南部的省份,中国其他地方的病例都是从“发源”地蔓延开来造成的。这一点充分说明了中国关于麻风病的传统认识的力量。这经久不衰的观点和西方关于种族退化的殖民话语相契合,部分地解释了为何中国精英没有对西方的观点提出任何挑战。 另一方面,在遗传问题上,受孕之时麻风“毒”就传给胎儿的这个说法,早在明清时期的医学著作里已提到,在中国南方直至年代依然为人深信不疑。在广西工作的医生李祖慰,年在一篇文章中根据日本研究者提供的资料,提出能说明孕妇子宫中有杆菌的证据,说明麻风病有可能通过遗传传染,反驳了大多数西方专家的理论。到了19世纪初,对遗传传染的信仰在中国南方已经变成根深蒂固,人们相信它不仅有脉络可寻,而且一代代减弱,最后到了第四代就停止了。此观念虽不载于清代医书,却似乎广泛流传于南方社会。 把这一关于遗传的通俗看法告诉外国人的不是别人,正式广东医生黄宽。黄宽显然相当重视此看法,在其年发自广州的报告中说,“麻风病人不和健康人通婚……麻风病人几乎所有的孩子都有此疾的症状。一般来说,此疾逐代减轻,到了第三代,除了脸色比较苍白,麻风病患者的后人已与常人无异。第四代已可以放心婚嫁,虽然这种事不常发生。只要婚姻局限于麻风病人之间,麻风病就呈自然消失之势。”显然,他所受的医学教育没有让他怀疑此看法的真实性以及在家乡的落实。 英国的作者们综合各种观察记录,然后心安理得地得出结论说:“几乎一致认为麻风通常有遗传性。”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和西方的麻风病观增强了麻风有遗传性,为特定地区和体质的人民所特有的观点。对中国人而言,南方人是主要的患者;而对西方人而言,所有中国人都是南方人。 书内插图 但是,麻风病的遗传说没有使西方的医生相信麻风病逻辑上会仅发生在中国和在中国人身上。相反,华人污染了世界的观点越来越有说服力。甚至在年汉森发现了麻风杆菌,为传染说提供了一条有力的科学证据之前,华人移民早已被指控把病传到了太平洋地区,尤其是夏威夷、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麻风病为中国特有的疾病的看法到了年代初已经根深蒂固,当时美国的舆论开始谴责华人移民把麻风病带到了美国。医院诊断出一名广州移民患有麻风病,年代初此事被认定是中国麻风病人“入侵”美国的开始。虽然旧金山的公共卫生官员试图通过重申当时的主流医学解释,即只有中国人会得麻风病,而且它只通过遗传传染,来平息公众的恐慌,但是人们依然歇斯底里。 夏威夷麻风疫情不断恶化的坏消息,使一些美国人确信华人移民正在将美国变为“麻风病人的国度”。实际上,在19世纪中期的夏威夷,麻风病通常被叫做“中国人的疾病”,人们认为在年华人移民开始踏上夏威夷群岛之前,当地没有这种病。一位叫做希勒布兰德的医生声称,他在年见到了他的第一个麻风病人。美国的舆论显然已经淡忘,欧洲人移民北美的早期阶段,欧洲大陆各地的斯堪的纳维亚、西班牙、英国和法国移民把麻风病输入美国的病例。19世纪晚期宣称华人到来之前麻风病已存在于夏威夷的报告,也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年莫里茨医生曾经发表文章说明年代美国传教士已注意到麻风病,甚至这样资料翔实、关于夏威夷麻风病史的文章,似乎也没有消除对作为麻风携带者的华人移民的恐惧。 夏威夷摩洛凯岛麻风病人墓地 在澳大利亚,“人们普遍认为是华人移民把麻风病带到了澳大利亚北部。已知北领地第一个麻风病人是华人男子,年有他患病的报告。”毫不奇怪,没有人研究像美洲那样19世纪之前欧洲移民已经输入澳大利亚的可能性。所以后来从年代开始,澳大利亚白人逐渐把华人和麻风病的传播联系在一起,开始限制华人移民并设置种族的防疫警戒线。 如前所述,不只中国感觉到了国际对麻风病传播的强烈抗议的影响,19世纪最强大、现代化程度最高的亚洲国家日本,也是此种国际恐慌的牺牲品,因为麻风病的存在似乎说明日本还没有完全有资格成为现代文明国家阵营中的一员。和中国一样,20世纪早期的日本媒体也宣传这样的观念:日本是“世界上麻风病最多的国家”,据估计有一百万麻风病人。作为一个殖民国家,日本也决心以美国建在菲律宾的麻风岛古岭岛为榜样,要消灭其殖民地“大东亚共荣圈”里的麻风病。同一时期,麻风病成了中国和日本意味着国耻的疾病。但是,20世纪早期,更强大、权力更集中的明治政府比中国的国民政府更有能力推行严刑峻法,把几乎所有的麻风病人隔离在像监狱一样的麻风院。通过此种做法,日本似乎向世界的其他国家说明了自己比其他亚洲国家文明、现代。 -年汉森发现了麻风杆菌,证实了麻风的传染性之后,白人国家面对所谓“中国人”或“亚洲人”的疾病入侵的歇斯底里变本加厉了。但是要到年,当在夏威夷工作的比利时著名传教士戴勉神父,在到麻风岛5年之后出现了麻风病的症状时,戏的高潮才开始。11年后的年,戴勉神父去世,在各大洲引起了极大的恐慌。麻风病的全球大流行似乎近在眼前。赖特的《麻风病:帝国的危险》也在这一年发表,它警告欧洲人再次患上麻风病的危险。从年代开始对麻风病大流行日渐滋长的恐惧,很快就导致了一系列针对华人移民的指控。它至少是年美国国会通过排华法案的一个原因,年华人也受到了澳大利亚同样的排斥,甚至哥伦比亚政府亦在年考虑禁止中国移民入境,虽然实际上当时该国并没有中国移民。在所有的喧嚣中,最尖锐的或许是康黎德的声音,他是梅森的亲密工作伙伴,也以在香港的医学教育工作而著称,在那里他和学生孙中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康黎德本人是位麻风病学家,在麻风病问题上撰述颇丰。在其著名的获奖报告“中国、印度支那、马来群岛和大洋洲的麻风病发生条件”中,他独挑华人苦力,认为他们是唯一需要为太平洋地区的麻风病大流行负责的人:“麻风不是太平洋任何地方本土的疾病,然而在麻风流行的三个中心肯定有某种共同因素。事实上唯一的共同因素就是中国佬,他是有麻风病的。”他说,华人移民完全缺乏“庄重和清洁”,“源源不断的移民的罪恶之一是麻风病的传播”。在他看来,控制这个局面的唯一方法,“那就是驱逐或严格控制所有中国苦力”。换言之,在许多有麻风病的有色人种中,中国人是世界的主要污染者,因为来自中国的移民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多。晚至年,孟买的印度政府雇佣的一个中国人因为发现有麻风病而被遣返回国,年之前,英属香港的麻风病人也被遣送回广州。 戴勉神父 把华人当做世界污染者的愈演愈烈的控诉,也是-年汉森发现麻风杆菌后麻风病的传染说最终战胜了遗传说的结果。不过,“胜利”在几十年之后才姗姗而来,而不是在此重要发现之后。 *选自商务印书馆,《麻风——一种疾病的医疗社会史》,作者梁其姿,有删节。 JIA 青年 成长 行动 改变 走进工作营 天下一家亲 一切都在静悄悄地发生改变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hthaituna.com/htwxtz/4710.html
- 上一篇文章: 神奇这种稀罕宝贝一年竟3次造访深圳海域
- 下一篇文章: 3月海豚服务之星丨温暖有爱的海豚人我们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