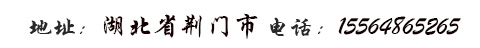白惠元ldquo红花疗法rdquo
|
《送你一朵小红花》电影海报 力匕 “红花疗法”与分享艰难 ——评电影《送你一朵小红花》 白惠元 文 阝勹 廴匚 摘要 电影《送你一朵小红花》以患癌少年韦一航与患癌少女马小远的青春爱情故事为主线,透视出两个当代中国抗癌家庭的日常生活风景。在这部“绝症青春片”中,导演韩延进行了一种有益的现实主义探索,揭示出中国式亲子关系的复杂性与当代性。从理性“鸡汤”到清醒造梦,电影成为了一则新冠肺炎疫情时期的国民心理寓言。经由“小红花”这一核心意象,我们得以洞见电影真正的情动机制:分享艰难。 关键词 《送你一朵小红花》;韩延;青春;情动;分享艰难 力匕 “红花疗法”与分享艰难 ——评电影《送你一朵小红花》 白惠元 文 阝勹 廴匚 电影《送你一朵小红花》拍摄于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后,目前票房成绩已超过14亿,近乎导演韩延同题前作《滚蛋吧!肿瘤君》票房成绩的3倍。几年之内,如此巨大的票房飞跃从何而来?中国电影市场的日渐繁荣与流量明星的主演策略自然是重要原因,但不可忽略的是,《送你一朵小红花》呈现出了导演前所未有的、分外强烈的社会表达诉求,用导演自己的话来说,正是“绝对质朴”“去技术化”[1]的现实主义风格。这或许是索解电影文本内部密码的关键所在。 电影《送你一朵小红花》以患癌少年韦一航与患癌少女马小远的青春爱情故事为主线,透视出两个当代中国抗癌家庭的日常生活风景。个中滋味,正如男女主角乐于配制的“暗黑饮料”,需要足够的勇气才能将其独自饮下。如果说,遇见马小远是对韦一航“丧怂”抗癌青春的梦幻治愈,那么尾声处马小远的疾病复发与突然离世,则宣告了痛楚的梦醒时分:现实主义的世界里没有奇迹。年2月3日,为本片创作同名主题曲的音乐人赵英俊因肝癌不幸离世,年仅43岁,这在文本之外更添沉痛。 诚然,一面是青春片的柔光滤镜,另一面是人间烟火的现实主义风格,二者确实构成了某种杂糅。事实上,这种分裂是与本片的曲折创作历程密切相关的。早在年,这一电影项目的立项初衷是翻拍颇受北美青少年欢迎的美国青春片《星运里的错》,并暂定由导演韩延担任翻拍片的制片人。年,项目名称变更为《初恋无可救药》,从故事梗概上看,依然是鲜明的翻拍方向:少年江亦凡在读高中时发现自己罹患脑癌,因患病而把自己完全封闭起来,此时,同样深陷癌症病痛的付文雅进入他的生活,并鼓励他去伦敦找前女友完成未了心愿,两人懵懂的爱情在旅程中展开。到了年6月电影正式开机,韩延成为本片导演,编剧团队加入了青年作家韩今谅,她的短篇小说《小红花》成为了本片展开创作的另一重要素材来源。 在此,本文无意于梳理分辨《送你一朵小红花》繁杂的创作源流,只是有必要说明,近年来世界影坛的“绝症青春片”风潮,包括剧本改编所依赖的文字资料,都应纳入解读坐标之内。更有意味的是,同期上映的影片《缉魂》和《小伟》(原名《慕伶,一鸣,伟明》)分别以科幻悬疑和家庭自传纪实的不同风格触及了癌症议题,相关题材影片的集中涌现恐怕并非偶然。相较而言,取得票房佳绩的《送你一朵小红花》有何独特性?它何以触动广大电影观众的心弦? “绝症青春片”: 源流、脉络及新变 若简要回顾世界电影史里的青春片序列,可将青春片的“发生”追溯至20世纪60年代席卷全球的青年反文化运动。在这场反叛运动中,以美国好莱坞为代表的商业类型电影和以欧洲电影节为代表的艺术电影双双诞生了青春片经典之作,前者如《邦妮和克莱德》(美国,),后者如《四百击》(法国,)。此外,表达战后日本青年愤怒状态的《青春残酷物语》()也可纳入其中。如果说,20世纪60年代青春片的根本目标是表达一种青年人对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困惑、疏离与反抗,那么新世纪以来的青春片则变得越发“安全”——以美国青春片为例,这些电影通常在接受既定秩序的前提下,在校园空间之内寻求合法化的、有限度的情绪宣泄,如结合性喜剧元素的《美国派》(美国,)、结合歌舞片元素的《歌舞青春》(美国,)、结合女性元素的《伯德小姐》(美国,)等。虽然也有《大象》(美国,)这样关于社会问题的尖锐表述,但整体趋于温和保守。 精彩镜头 SHOTS 上:邦妮和克莱德 下左:四百击下右:青春残酷物语 或许是呼应,年以来兴起的、多上映于暑期档并且收获高票房的中国青春片延续了这种保守主义表意策略:通过中年怀旧的抒情语态,重返光滑、美好、精致、可爱的校园青春时代。我们观看青春,就像观看电影《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结尾处海洋馆里的海豚,我们透过一个安全的玻璃罩进行自我审美,此时,绝症、堕胎、出国等常见“疼痛青春”元素不过是一面面怀旧的柔光滤镜而已,它们共同渲染了青春的感伤氛围。有趣的是,近年来一些中国青春片开始摆脱怀旧色彩,讲述现在进行时的青春成长经验,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诉求与清晰的社会问题角度,如《狗十三》()、《嘉年华》()、《过春天》()等,它们标志着中国青春片正在从“海豚时代”游进“鲨鱼时代”:“生猛、危险、迅疾,有行动力,有攻击性,有毛边,有利齿,会出血。”[2] 精彩镜头 SHOTS 上:过春天 下左:狗十三下右:嘉年华 显然,《送你一朵小红花》属于后者,它是有锐度的,是把癌症家庭当作社会切片来进行显微观察的,尽管它依托于“绝症青春片”的一些重要类型要素。因此,要深入拆解电影的叙事策略,仍需回到其类型基础层面。所谓“绝症青春片”即放大疾病元素(及其死亡效果)并以爱情为治愈方案的青春电影,通常展现为“癌症+青春”的叙事模式,肇始于21世纪初的日韩“纯爱电影”。“纯爱电影”主要表现青春期少男少女之间的纯洁恋情,通常以生死相隔的悲剧收尾。如何理解“纯爱电影”里的“纯”字?究竟什么样的爱情才称得上“纯爱”?以《在世界的中心呼唤爱》(日本,)、《我脑海中的橡皮擦》(韩国,)、《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韩国,)等经典“纯爱电影”为例,所谓“纯爱”,正是剔除了性、物质、阶级等社会因素之后的情感乌托邦,观众沉湎于柔光滤镜中的爱情童话,与之共欢笑共流泪,最终达成了一种抚慰疲惫心灵的“净化”效果。为使“纯爱”具有不可替代的永恒意义,此类电影的主人公通常因患有绝症[3](癌症、失忆等)而进入生命倒计时。于是,少男少女的青春能量因病痛生命而迸发出极度绚丽的光彩,这是一种典型的日本美学,灿烂如樱花,速朽如樱花。 然而,当日韩“纯爱电影”风潮波及欧美青春片,叙事重点却发生了有趣的偏移:叙事主题从爱情变成了疾病。在《抗癌的我》(美国,)、《星运里的错》(美国,)、《我和厄尔以及将死的女孩》(美国,)等一系列美国青春片中,疾病变得真正在场,它深锲于主角的身体造型之中,并时刻提醒观众,回归无法美化的痛感现实。以电影《星运里的错》为例,16岁女孩Hazel因肺癌自始至终插着鼻管,并拖着沉重的氧气瓶到处奔走,而她热爱运动的恋人Augustus则因骨癌而装上假肢,如此刺目的身体造型设计,使爱情童话的唯美光晕褪去,也让电影的叙事风格多了几分冷静克制。无独有偶,电影《抗癌的我》与《我和厄尔以及将死的女孩》也都通过主人公的化疗剃发场景来传达一种写实主义诉求,创作者试图由此告知观众:青春之美在于顽强乐观克服病痛的生命意志,而非肌肤光洁的初恋之吻。必须指出的是,虽然上述影片的叙事重点转移至疾病,但爱情并未消失,青春之恋依然行使着治愈病患心灵伤痛的戏剧功能。因此,这类绝症青春片很容易滑入一种“小妞电影”(chickflick)的窠臼:制造一处浪漫偶遇,怀抱一个共同梦想,策划一次异域旅行,举行一场疯狂告白,遭遇一回冲突误会,最终实现治愈和解。无孔不入的流行音乐与无处不在的小清新画风强化了其都市时尚感:“它们共同营造出一个美丽的幻境,体现出中产阶级和小资/白领的审美趣味和期望。”[4] 精彩镜头 SHOTS 上:抗癌的我下左:星运里的错 下右:我和厄尔以及将死的女孩 谈一场恋爱就能治愈绝症之痛吗?许多创作者(尤其是男性创作者)不以为然,他们拒绝“小妞电影”的惯常套路,尝试打开绝症青春片的喜剧空间,融合更多喜剧类型。电影《最爽的一天》(德国,)讲述了两位阶级对立、性格迥异的男性癌症患者的自驾非洲之旅,用公路喜剧的方式铺展处处笑料,最终治愈彼此的是友谊。而电影《伟大的愿望》(韩国,)则以性喜剧的方式,讲述了两个高中男生帮助身患渐冻症的好友实现最终遗愿的温情故事,该片的中国版《小小的愿望》也在年上映。可见,创作者的性别立场差异将会导致青春片情动模式的区分,男性向青春片与女性向青春片有着截然不同的情动机制[5]。具体到绝症青春片这个亚类型,男性向创作者更倾向于将绝症视作触发遗愿的人物初始动机,绝症相当于剧作加速发展的倒计时钟,它首先是戏剧功能上的“绝境”,而超越“绝境”的方法可能是旅行、探险、醉酒乃至斗殴,唯独不是谈恋爱。在这个意义上,《送你一朵小红花》糅合了以上两种绝症青春片的创作旨趣:既有女性向的纯洁恋情,也有男性向的探险冲动,甚至还有对性少数群体(吴晓昧及其已故恋人)的隐秘书写,故而达成了对不同性别分众的多向迎合。 精彩镜头 SHOTS 上:最爽的一天 下左:伟大的愿望下右:小小的愿望 除此之外,本片的另一大创作目标是在绝症青春片的既定框架之内进行现实主义探索,这在影片的形式与内容层面均有所体现。先看形式,导演韩延放弃了此前电影作品里一以贯之的二次元视觉风格,仅存的cosplay主题追思会场景也因男主角充满戏谑的视频直播而被解构。在色彩光效上,本片也与其绝症青春片前作迥异。不同于《第一次》()的校园文艺小清新,也不同于《滚蛋吧!肿瘤君》()的都市时尚童话,两个癌症家庭的居家场景设计都有一种褪去都市光泽后的粗粝质感。无论是韦一航周围的旧家具,还是马小远居住的修车行,这些空间都着力展现普通人柴米油盐的日常生活,尤其是直面癌症家庭并不富裕的现实经济状况。再看内容,《送你一朵小红花》对前作的超越性集中体现在对韦一航家庭关系的写实描绘上,这使得本片成为了真正的中国故事:孩子得病,奶奶要卖房,全家两代人集体上阵帮忙;为了给孩子治病,妈妈只能吃烂菜叶、逃停车费,爸爸偷偷开专车挣外快,连一口热饭都吃不上。正是由于太害怕失去,愤怒的爸爸才会对儿子说:“你的身体不光是属于你的,还是属于我们的!”这是典型的中国式亲子关系,父母如此沉重的奉献、牺牲乃至情感绑架,很难不激起子女更深度的亏欠感。 两相对照,美国电影《星运里的错》同样设计了一场提前预演的亲子告别戏。女主角得知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便追问妈妈:如果她真的死了,父母该怎么办?她害怕父母因为失去她而变成行尸走肉。出乎意料的是,妈妈含着眼泪回答:“失去你会让我们痛不欲生,但是大家都知道,再痛苦也要继续生活。无论如何也要活下去。”或许是借鉴于此,《送你一朵小红花》设计了同样的问题,并由韦一航抛给父母,而父母的回应方式则是自拍一整天生活vlog(视频网络日志),这是妙趣横生的一笔。在亲切、诙谐、温暖的氛围中,令人窒息的中国式亲子关系得到了暂时解脱。可以说,对中国癌症家庭关系的深度挖掘是本片现实主义风格探索的立根之本,也是打动普通观众内心世界的关键所在。特别是对独生子女平民家庭日常生活的聚焦,使得本片展露出《第一次》《滚蛋吧!肿瘤君》所不具备的当代中国性。 “红花疗法”: 理性“鸡汤”与清醒造梦 如果爱情不能治愈病痛,那么,画上一朵小红花就可以吗?电影的结尾几乎是一种泛神论场景:马小远死去一年后,韦一航终于来到幻觉中的青海盐湖。他先是看到了“平行时空”里的自己——穿着白衬衫牛仔裤的韦一航与一袭白裙的马小远相聚于此,他们没有病痛,欢笑玩乐,仿佛是对电影《大话西游》结尾的再次搬演,也令人想起英国剧作家尼克·佩恩(NickPayne)的获奖名作《星宿》(Constellations,中国版译作《平行宇宙爱情演绎法》)。我们之所以需要“平行时空”,不正是因为现实世界充满遗憾吗?想要超越此时此地的生死离别,我们只能卑微地借助想象中的超自然力量。于是,才有了韦一航的极目远眺。他突然看到了湖畔山坡上的一群羊,每一只羊身上都画着一朵五瓣圆心的小红花。他将目光锁定在一只小羊身上,凝视着红花图案,那一瞬间,曾经在自己手背画下小红花并给予他温柔鼓励的马小远似乎与他重逢。万物有灵,天高海阔,《送你一朵小红花》终结于一场奇迹。 如何才能让癌症患者相信奇迹?韦一航曾经对“奇迹”嗤之以鼻,他在病友互助会上对张大师精心写就的心灵鸡汤冷嘲热讽,原著小说《小红花》里设置的这个场景几乎原样搬演到了电影之中:“人们暴露出各自的残破,期待着各自的奇迹,而张鹤松只是弯腰抱出又一摞书。韦一航只觉得气血翻涌,上前抽出那张‘酸’,在拳手里攥成一团,扔在地上说,什么叫奇迹啊,奇迹是一觉醒来这一切都不存在,是我不用拖着天旋地转的头担惊受怕,是他的两条腿失而复得,是她一家三口阖家欢乐,是肿瘤从来没来过,你不用一分钱掰成两半花,也不用疼得睡不着觉。”[6]但是,马小远却捍卫了“鸡汤”的必要性:“都是活不长的人,吗啡都能上,喝点鸡汤过分吗?”[7]显然,在癌症患者的生命语境内,“鸡汤”并非蛊惑众生的心灵按摩,而是病友们的理性选择:明知其虚假,但依然喝下,因为他们太渴望奇迹能够发生在自己身上,而“鸡汤”就是一场迎接奇迹的祈祷仪式。虽然马小远已经死去,但韦一航在影片结尾处迎来了自己的奇迹时刻。 究竟该如何看待《送你一朵小红花》如此魔幻诗意的结尾?我们不能奢求每个癌症患者都能迎来奇迹,但电影艺术永远呼唤奇迹,尤其是在结尾处。回顾世界电影史,最著名的结尾奇迹恐怕就是“最后一分钟营救”了。在《孤独的别墅》()、《一个国家的诞生》()、《党同伐异》()等电影作品中,美国导演格里菲斯通过将不同地点、不同视点、同时发生且具有因果关系的一系列动作进行交叉剪辑,形成了一种加速发展的电影叙事效果,最终达成了电影史上最著名的结尾奇迹。正如大卫·波德维尔所说:“虽然很多导演都曾用过交叉剪辑的方式来简单交待救援者与受害者之间的救援行动,但格里菲斯之所以著名是因为他将这种叙事手法——最后一分钟营救——发扬光大。”[8]然而,癌症电影又是非常特殊的,它的结尾往往是无法营救的最后一分钟,甚至从电影的第一分钟开始,主人公就已经开始练习与这个世界告别,而观众的心中就已经开始集聚死亡的乌云。所以,造梦成为了一种必须:主人公迫切需要超越此在的肉身局限,经由精神漫游奔向自由。 《星运里的错》用一场梦寐以求却不尽如人意的荷兰之旅告慰了女主角的内心遗憾,《我和厄尔以及将死的女孩》用一部由男主角重新剪辑的自制粗糙电影送别了女孩的弥留时刻,相比之下,《送你一朵小红花》的造梦场景更多了几分清醒。为了实现韦一航走遍世界、徒步探险的愿望,马小远精心策划了一系列“原地穷游”:他们在海鲜市场嗅闻南非干斯拜海滩,在冷鲜冰库想象南极,在修车行蓄水池体验死海,在旋转楼梯攀登喜马拉雅山脉的冰川溶洞,在布满鼓风机的顶楼感受科罗拉多大峡谷,在建筑工地跋涉撒哈拉沙漠,在高空缆车眺望火星,在广场喷泉穿梭委内瑞拉天使瀑布……这样清醒的造梦时刻仿佛是在电影银幕上还原了一种剧场体验,即在极其有限的舞台条件下,两位恋爱中的主人公都坚信舞台的假定性,他们用演员的信念感充分打开了自己的各种感官,他们没有观众,他们只为彼此表演。而摄影机的推拉运动又无时不刻不在提醒观众:他们哪儿也去不了,他们的肉身从未走出此地,这样的“旅行”不过是一场两情相悦的过家家游戏,它简陋、质朴却又无可奈何。猛然间,一种微妙的共情就此发生——这不正是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的个体生命体验吗?我们无处可去,我们无从流动,我们日常隔离,我们只能在视频网站博主的手机自拍中进行云端虚拟漫游。 从理性“鸡汤”到清醒造梦,电影《送你一朵小红花》不期然地成为了一则新冠肺炎疫情时期的国民心理寓言。为了抚慰民众的焦灼感,创作者给出的治疗方案是“小红花”。回到影片中,马小远的理性“鸡汤”最终融化了韦一航的酷寒心防,她劝慰他不要“怂”,要积极起来,因此,她在他的手背上留下了一朵小红花。虽然他们都明白,这朵小红花带来的力量必然是十分有限的。原著小说将“小红花”的花语定义为“假积极”:“韦一航和盘子里的仙鹤对了会儿眼,问,小红花不是哄幼儿园小孩的吗?看方远儿瞪过来,小声补充,我又没拿过小红花。见两人不信,韦一航只好解释,我学习不主动,劳动不自觉,吃饭不带劲,睡醒没精神,总之人生就没当过积极分子,小红花要是有花语,不就是假积极吗?”[9]在这里,“病”不只是电影文本里的癌症实体,也是疫情时代全球民众的心理隐喻。斯洛文尼亚思想家齐泽克曾经断言启蒙的溃败,并毫不留情地批判犬儒主义理性:“人们很清楚那个虚假性,知道意识形态普适性下面掩藏着特定的利益,但他拒不与之断绝关系。”[10]但是,《送你一朵小红花》似乎给出了另一种解释:在如此特殊的历史时刻,在全球瘟疫的阴影之下,我们明知小红花之虚假,却仍愿为彼此赠予温暖鼓励。正如歌中所唱:“送你一朵小红花/开在你心底最深的泥沙/奖励你能感受/每个命运的挣扎。” 《送你一朵小红花》剧照 分享艰难: “同病相怜”的情动机制 电影《送你一朵小红花》的片尾字幕时刻颇值得玩味:首先是片名浮现,接着,片名上方出现了清晰的时间标记,这当然是导演有意为之,他试图用影像记录时代,并借由本片与疫情时代的国民进行心灵对话。而当演职人员表开始滚动之时,画面左侧渐次播放一系列短视频画面:被学生簇拥陪伴的生病支教老师、得知同事病危却坚持治病救人的抗疫医生、受了委屈止不住流泪的服务员、罹患脑瘫却坚持工作的外卖小哥……这似乎传达出创作者强烈的社会关怀诉求,相应地,影片文本内部的癌症也就被转喻为普通人的普遍苦难。有趣的是,任凭短视频画面如何更迭,下方的文字却始终坚如磐石:谨以此片献给积极生活的我们。 《送你一朵小红花》片尾字幕 显然,导演不满足于只讲一个癌症故事,他要在更广泛的维度上与社会大众实现深度共情,而这个情动机制就是“同病相怜”。从追思会、病友互助组到红花羊群,电影始终在建构一种共同体图景,而男主角韦一航的人物成长弧光正在于他对共同体从拒斥到融入的全过程。如此说来,影片结尾处印有红花图案的小羊也就不只是马小远魂兮归来,更是韦一航自己的精神镜像。在影片中,韦一航曾以相当不屑的语气对着纪录片摄影机念出一段写好的口播,但到了最后,他反而成为了这段宣言的信仰者,因为身上的红花图案让苦难者彼此识别:“每个人都不是一座孤岛。虽然病痛让我们彼此距离更加遥远,但分享和互助就是联系每个人的链条。我们要和癌症化干戈为玉帛。”[11]正因为“同病相怜”,我们更要彼此“分享艰难”,这就是电影片尾短视频画面的叙事逻辑。 作为一种话语,“分享艰难”需要被历史化,它曾经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的时代格言。刘醒龙的同名中篇小说《分享艰难》()讲述了90年代初中国农村面临的多重困境:为解决财政危机,鹿头镇镇长孔太平只能用抓赌的罚款去发放已拖欠数月的教师工资。尽管有几分失落和无奈,他却在尽力为国家“分享艰难”,这四个字不只是对孔太平的描述,更是对时代的有力呼吁。由此,刘醒龙与谈歌、何申、关仁山等作家共同掀起了当代文坛充满忧患意识的“现实主义冲击波”。年,引发收视热潮的电视剧《雍正王朝》上映,这是中国大众文化场域对“分享艰难”四字格言的有力回应。从现实主义小说到帝王剧,90年代中国的这句响亮口号预设了一种核心角色:“当家难”的领导者形象。20年后,当“分享艰难”的声音再次响起,喊出口号的主体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年的网络流行语“我太南(难)了”“”到年的年度热词“打工人”,再加上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对劳动力市场的全面冲击,真正需要“分享艰难”的正是作为普通劳动者的我们。当身体的病痛被转喻为日常生活的艰难,电影真正渴望送出的红花式鼓励也就渐趋清晰:与其说“积极生活”,不如说努力劳动。 如此劝慰表面上是温暖的,其实是可疑的。毕竟,此“病”非彼“病”。若把二者等同,则遮蔽了这种“艰难”背后的社会政治经济因素。那么,这样一部绝症青春片也就不只是一种“情动经济”(高票房收益),更是一种“情动事实”[12](affectivefact):它通过情动机制实现了一种操作逻辑(operativelogic),这种“同病相怜”的情动机制固然能够暂时抚慰人心,却更容易产生规训功能,使观众在感动的泪水中忘却自身潜藏的能动性。我们理应对此保持警惕。 注释 [1]韩延,田卉群.“小红花”:向死而生——韩延导演访谈[J].当代电影,(2):31-39. [2]活字文化.白惠元专访:中国青春片从“海豚时代”进入“鲨鱼时代”[EB/OL].(-12-04)[-12-05].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hthaituna.com/htbhjb/8191.html
- 上一篇文章: 今天,白海豚再现梧州西江水域,很多梧州人
- 下一篇文章: 心疼梧州白海豚身上因感染造成的斑块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