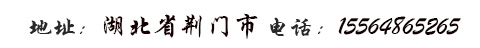李爱民吃甜秆青玉米秆
|
文章来源:李爱民文艺仰韶 吃甜秆 文/李爱民 你虽然吃过甜秆,恐怕对甜秆知之不深吧!甜秆,俗称“哑巴秆”,是不结穗的青玉米秆。这种玉米秆不知什么原因不结穗,充其量只结个“粒涨娃”——就是稀啦啦不几个籽的玉米穗。可能没有把能量转化成果实,玉米秆自己“扪心有愧”,就把糖分集中在下半部。这部分水分含量高,且甜脆可口,简直就是“小甘蔗”。甜秆的生命力很强大,直到玉米收获季节它还是青枝绿叶的,向人们报告她是甜秆的消息。我母亲给生产队掰玉米时,总能挑出一些甜秆来,至今记忆尤深。当然,我也经不起“小甘蔗”的引诱,常常和伙伴们一样去“害践人”,偷一些甜杆吃。 ——姚俊注 小时候,我们农村生活困难,家家粮食不够吃,吃零食就成了奢望。但孩子们天性不安分,于是我们向大自然索要能入口的东西。生洋槐花、绿绿葱、黄花苗、茅草根、棱草根、酸布叽草、麦莲籽种籽、羊角果、枸桃、软枣等等,我们常常取其能吃的那一部分,或酸或甜,品一点味儿,过过嘴瘾,缓解一下饥饿就成了。 而甜玉米秆(甜秆),则是我们野外吃零食中的首选大餐。甜秆是我们渑池人对青嫩玉米秆中含糖量较高的那部分玉米秆的通称。一块地里甜秆很少,尤其雨水好的时节几乎没有,天旱时较多。那时根本吃不上南方的甘蔗,所以拿玉米秆替代,还有一种高梁秆更甜,但很少有人种。啃青玉米秆,除了顶饥止渴,那时还是一种乐趣。 每年秋季,一棵棵玉米株像一个个身着军装的士兵站在农田里,绿油油一片。玉米棒子齐刷刷地像战士手持的战利品一样,等待着乡亲们检阅验收。秋风习习,玉米株恰似跳广场舞的绿衣女郎,随风起舞。这些美景对经常饿肚子的半拉小伙子来说自然是无心享受的。我们需要的是在玉米地里寻找带甜味的玉米秆或玉米棒,来解决饥肠辘辘问题。但生产队到处安排人看庄稼,大人不允许我们小孩子糟践庄稼,所以吃甜秆很难。即使大人放开让我们去找,一大片玉米地中,可以食用带甜味的青玉米秆很少。我们经常和看庄稼的人“打游击”。在他们的视野盲区,迅速折上一根玉米秆,哪怕没有甜味,我们也会大口嚼上一通。被逮住了,会被教训一番,或挨几下揍,就把我们撵滚蛋了。饥荒岁月里没啥吃,看庄稼的人对孩子们大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没那么较真。 但也有例外。有一次,我同几个小伙伴在我们队老北地的玉米田里,发现一片玉米秆发红且不太粗,我们凭经验知道这里的玉米秆肯定很甜。折下一棵尝尝果然香甜多汁。我们欣喜若狂,正要大开杀戒折甜秆时,一双大手一把揪住我们胳膊,回头一看原来是生产队的看地人老坷垃。老坷垃快五十岁,是个老光棍,为人处世一根筋。大家说他性不真,不够数。他让我们三个小伙伴站在地头大太阳底下,先踹我们一人一脚,再扇我们两巴掌,然后要我们背毛主席语录。我们一边哭,一边背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正好,我父亲和几个社员去地里干活,瞅见了我们。他上前质问老坷垃:“娃们咋啦?” “他们破坏抓革命促生产,折玉米秆。”老坷垃理直气壮地说。 “你扣这帽子可真不小,干脆你把他们杀了算了。”父亲一看我们脸上有手指印,一把抓住老坷垃的衣领,怒斥道:“多大的事,你下重手打娃们干啥?” 同行社员连忙拉住我父亲说:“一个队里,至于这样吗?”并对老坷垃说:“娃们家,折两根玉米秆,你凶凶算了,干吗这么折腾娃们,还下手那么狠,你不怕遭到报应吗?” 老坷垃显然觉得自己做得过了,便不再做声,从人群中缓缓向一边走去。 父亲对我们说:“你们也是,就是再饿,也不能祸害庄稼啊,就不能忍上两天,掰玉米时候你们随便找甜秆吃,都回去吧。” 我们几个低着头向家走去,这一幕一直刻在我心中。 没多久,开始秋收掰玉米了,我们帮大人掰玉米,还在地里到处找甜秆。有时找到一大堆,我们就抱回家,但又不能长时间存放,没几天甜秆就变老不能吃了。这时还能吃上平时难以吃上的嫩玉米,烧熟或煮熟,香甜爽口百吃不厌。 有一年天大旱,玉米没成熟,地里甜秆很多,生产队里还分些嫩玉米,我们少年不知愁滋味,欢天喜地地吃甜秆。大人们却愁容满面,一个灾年要来临了,日子该咋过呢? 一晃四十多年过去了,如今玉米甜秆几乎没人吃了,取而代之的是南方运来的甘蔗,以及各种水果,就这些人们都吃腻了。人们发愁的是不知该吃啥。那种老甜秆的味道,依然深深地烙印在脑海里,挥之不去,拂之还来。 作者简介:李爱民,网名剑客,年生,渑池人。义马作协会员,酷爱文学,从年9月起,在各自媒和纸媒,发表散文、小小说、诗歌及时评余篇,其中两篇文章分别在巜三门峡文史资料》30期、31期刊发。喜欢诗与远方,信奉吃亏是福,真诚无敌。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hthaituna.com/htwxtz/11380.html
- 上一篇文章: 枣花蜂蜜和洋槐蜂蜜哪个好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