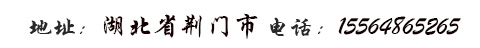游戏四
|
sideBDifficulttobe 选择幸福,和被幸福所选择,是两码事.而不曾拥有,与拥有后再失去,后者要痛苦得多. 她曾经一度认为,乌干达的夜空永远星光灿烂,像是世界混沌之处没有被污染过的眼睛,明亮绚烂,像是某人执著的眼. 吃过晚饭后,兰和大家一起收拾着碗筷,工藤和她说着什么,黑发的女子温柔地笑,脸上的表情神采飞扬. 没有人知道,她的心上,打着一个死--死的结. 新一不一样了,那种自信的,阳光的感觉还在,可就是有什么地方不一样了.也许是他过于温暖的眼神,也许是那种太过平和的表情,反正就是不一样了. 让她既熟悉,又陌生的新一,本能地想要抓住,让他不再离开. 当她从博士那里得知他在乌干达时,心里有些凉,但还是很快的调整了过来,她知道那个茶发女子不同寻常的身份,知道他们曾一起经历过的那些自己无法涉足的苦难,所以她能够理解,但不知为什么,很冲动的,她也到了这里来. 并没有什么太深的意念,她只是想要看一看,那个漂亮的茶发女子,和新一,所执著的东西. 可她看到这里简陋的环境和那些病人的时候,她还是本能地想要闭上眼睛,不去看那些流血的伤口和因痛苦而变形扭曲的脸. 是灰原站在她的身后拍了拍她的肩膀,扭过头对新一说你干吗带她到这里来,一般人怎么受得了,然后拿着纱布和药酒去为病人们清洗伤口换药,脸上一直带着笑容. 就是那种极淡定,极疏离,却又极其优雅的笑容. 她用修长的手指为绷带打一个漂亮的结,她用清冷柔和的声音和每一个人打招呼,她像是早春的晨光,夏日的清泉,是无比美好的存在. 就像现在在桌子的另一边,她的周围围满了护士,她们众星拱月般的围着她,脸上尽是开心的笑容. "怎么了,兰?"他的声音在耳边暖暖的响起,"楞什么呢." "没什么."她笑笑,回答道. 灰原有在晚饭后出去散亇 步的习惯,兰看见她的身影在夜色里朦朦胧胧的勾勒出了一个美好的轮廓,医院,向着她的方向跑了过去. 她只是想问问新一好不好,就这么多,就只有这么多. 在距离她几步远的地方,她停下了脚步,微微喘着气,面前的茶发女子像是早就知道她会来似的,慢慢地转过了身子,对着她缓缓的一笑. "怎么了?"灰原问道,一面摘下手机的耳麦. 四周除了青虫鸣叫的声音,什么也没有,天上的星星和黑夜无声的注视着她们,干燥的风不留情面的吹起她的长发,她的表情有些惊慌,带着些许的犹豫和不确定,心事重重. "如果你有话想对我说,那么我很愿意听."她的声音清冷至极,她的右手斜斜地插在牛仔裤的口袋里,她的整个人站在那里就像是一幅上好的名画,颜色不浓不淡,明暗恰到好处,浑然天成. 她觉得自己的声音都在颤抖,她只是开口叫了她的名字眼泪就落了下来. "小哀......"她自己似乎也有些不知所措,急忙用手背抹去眼泪,却看见一方洁白的手帕递到眼前. "呐,把眼泪擦掉."灰原说道,"我知道你想对我说什么,我都知道."她看着兰惊愕的表情,轻声笑了. 她觉得自己从来都没有笑得这么努力过,好像浑身的力气都用来支撑着一个唇角微小的弧度,而全身的血液却在一瞬间涌上大脑,不停地击--打着她的神经. "你不用担心."她转身走开,留下这么一句清淡的词措. 乌干达的夜风把她的悲伤不知吹向了何处,她微笑着,脚步坚定,她早就知道了,所以她可以接受.不会很难. 只是那些星星,那些从来都无声闪烁着的,亘古不变的星星,去哪里了呢? 之后的生活平淡无奇,灰原不再让他接手过多的工作,而是选择自己一个人来,丢给他的通常都是整理病例,药物分配之类的事情,他抗议,她无视,“那些你可以和兰一起去做。”这就是她的解释,他听了以后心中无比难受,却又不能说出口。 于是在很多个有着明媚阳光的清晨,或是闷热的让人倦怠的正午,还有金黄落尽的凄艳的傍晚,他都有意无意的看到那个家伙瘦削却挺拔的倔强背影,默默地忙碌着,眼角眉梢都带着那么一丝若有若无的隐韧,还有落寞。 他就这么手足无措的看着她走远了。 是,他喜欢兰,他也应该喜欢她,她具备了所有优秀女孩应有的条件,她温婉美丽,她心地善良,她曾经那么不离不弃的等了他那么多年,她没有不好,这一切他也都看在眼里。可她呢,那个同样一直以同伴的姿态陪伴在他身边的,冷语相向却是真心相待的她,灰原哀。 自己对她那份同伴之间的关心,究竟是什么时候变质的呢? 他不知道,那么她来为他解答。 她从来都是看得最开的那一个。 她明白默默等待的苦楚,已清楚追随而至的勇气,所以她不能让他对那黑发的女子有所辜负,她不能。所以她冷漠,她回避,她可以爱他,但是他不可以。他的心应该只属于她,那个与他相伴十几年的善良的,像天使,像海豚的她。 他们之间的对话,少得可怜,寥落的十个手指也数得尽,她也不再那么频繁的微笑,稀少而又短暂的笑容,都在病房里消耗殆尽。 他的心痛得紧。 明明尚未离开,他就开始想念,想念那个清冷而美好的女子,想念那张明丽,素淡的笑颜。 而时光,会不会消磨掉想念。 这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一种叫做永恒的东西,灰原哀从来就是这么认为的,还有那些关于梦想,希望,正义之类的东西,她也不怎么相信。 最好的证据,就是以前在组织里时,一个人要被处死,就送到了她这里来当试验品,那人一直带着倔强地表情说着什么正义总会战胜邪恶,听得她闹心,撂了一句话过去:“那我还是用氰酸钾帮你实现愿望吧。” 可是谁知道呢,她爱上的,竟然会是坚信真理与正义的人。 日本的大学开学在即,他们就要走了。 走了好,就清净了。她坐在窗前默默地想着,一面擦拭着原本就很干净的手术刀,银冷的光映衬着她惨白的脸,漂亮的眼眸沉静的像北欧森林中深不见底的冰蚀湖。 晚上有给他们的送别晚会,现在还不到五点,也不是很忙,她还可以再睡一会。恍惚中,她隐约记起好久以前和姐姐见面时,姐姐笑着问她,她说志保你相不相信这种事,就是你失去了一个人,你就会觉得生无可恋?姐姐的表情既痛苦又认真,可却还在微笑着。 而她,慢慢抬起眼,回答说:“我不信。”声音清冷,不着感情的痕迹。 是,她怎么可能相信,又有什么资格去相信。冷言冷语风刀霜剑,生她长她的环境,让她从来都只相信自己,地球不会离了谁就不再转动,人也是一样,哪怕独自一人众叛亲离也得挣扎着活下去。 而她姐姐却不同,在她生命即将终结的瞬间,她想起的,也依旧是赤井坚毅的背影和妹妹完美的侧脸。 她死的遗憾,而她却活得痛苦。 其实,她也曾经想过要用自己的力量将姐姐留住,她不相信她会离开,可为什么在这个世界上,就总有一种东西,它的名字叫做事与愿违。 所以在那以后的那么长久的岁月里,她看着他总是拼尽全力去寻找真相时,真想一巴掌打醒他,告诉他这世界上哪有什么绝对的真相,而且所有事如果只要努力就办得好,那么这人生还真是简单的不是一点了。 可他偏不懂,一直前进,勇敢而能够保持梦想。 是不是她太世故,把世界看得太透彻太明白。 是不是他太天真,把人生想得太干净太美好。 那句话是怎么说的来着? ---你把世界看错了,却反说它欺骗了你。 恍惚着,她忍不住想笑,这是什么样的浑噩世界。 她从臂弯里抬起眼,望着非洲大草原在一天的生机盎然之后的倦意,夕阳橘色的光辉暖暖的照,从窗户里看到的天空是如此的小而狭隘,似是硬生生的,将她同外界隔了开来。 不管是从前,还是现在,我们都不属于一个世界,工藤。 她抬起手扶着额头,看了看手表,快六点了。 她走出去,人们忙碌着准备着当晚的送别晚会,走近了想要帮忙却被大家拦住了:“灰原医生你回去歇着吧,这里我们就行。”他们脸上挂着汗水和笑容,是让人无法拒绝的真挚。 “好啦,我回去还不行吗。”她笑着,转身回到病房。 井上坐在一个低脚凳子上看书,一旁病床上的孩子睡得很安稳。 “井上。”她走过去,轻声叫她。 “哎,灰原医生,你来啦。”井上抬起头,脸上带着她那种常有的明朗的笑。 “你怎么在这,我当你还睡着呢。”灰原弯下腰,看清了井上手里的杂志,揶揄的笑了,”果然还是Vogue更有吸引力。“ 井上笑着斜了她一眼,说着什么嘛,这都是去年的了,这里怎么可能买得到啊。灰原看着封面上那个金发碧眼的时装模特,也笑了。 “我说灰原医生,你一定没有后悔过到这里来。”井上突然盯着她,十分肯定的说。 “嗯?怎么这么说?”灰原饶有兴致地勾起嘴角,问道。 “因为我有的时候会很后悔。”井上把杂志丢在一边,伸了伸懒腰,“因为这里的生活这么苦,而且无聊……不能逛街上网也不能打游戏,很郁闷啦~”她看见灰原的视线停在那本杂志上,接着说,“虽然以前也不会买那些名牌可是看着商店橱窗里的新品也超级有安慰的……”灰原轻声的笑了出来,“怎么嘛灰原医生,你还笑。你这腕表不就是去年Prada的限量版么……” “那为什么会选择到这里来呢?我看你的简历上写你已经在米花中央病院工作了啊。” 井上的神色突然有一瞬间的异样,可随即她又拉开一个惯有的笑容,大大咧咧地说:“人生,不就是要有点追求嘛~”她笑得很无赖,“后悔是有,可我舍不得走。” “这里的人都很淳朴,比呆在东京要自在的多哦,灰原医生,你也是这么想的,对吧?” “嗯,差不多。”灰原看着井上稚嫩年轻却是无比爽朗的笑脸,回答。 为什么我周围的人都向往着光明,而我却一直站在黑暗中呢。井上说的对,她不曾后悔,因为她想,她是来赎罪,又怎么会后悔。她想洗去手上心上沾染了十几年的血腥,以此告慰那些该死或不该死的亡灵。 她怎能后悔,否则不又是一次逃避。 她从组织逃到东京,从东京逃到乌干达,哪里都不是她的归宿。 所谓归宿,也只是无依无靠却有所牵挂的人,才会向往的地方。 她是吗? ---谁知道。 夜幕降临,医院门口,工藤和兰迎面走来,他们下午去订机票. 模糊的暮色中,她看着站在他身边的兰,衣着鲜丽,神采奕奕,挽着工藤的手,脸上带着平和却又幸福的笑容,完全不属于这个地方. 他们就应该回东京当他们的大学生,悠闲自在无法无天,那是他们的生活. 她只想守在这里当她的医生,不愿再离开. 为什么要划分如此明了的界限. 她撇撇嘴,走了过去.脚步轻快,像是踩着精准的乐点. "订到了没?"她问道. "嗯,明天下午3点."他回答,"今天忙不忙?" "不,很闲."她避开他的目光,"晚会快开始了,你们过去吧." "你呢,一起走吧."他说着.兰也对着她笑着说是啊小哀,一起走吧. 你是瞎子还是呆子啊...她有些恼怒地想着,淡淡地看了他一眼,"不了,我要去叫井上."说完转身走开,眼里写满不屑. 总是会到来的啊. 她没有去找井上,而是独自一人爬上了附近的一个小山坡.敲鼓和唱歌的声音传来,被风音阻挡的不大清晰.明亮的火光燃烧着跳跃着,远远的看过去像是一点点暖和的灯光.于是她在山坡顶处躺下,仰面望着天空. 整个天空在无数繁星的点衬下,透着深沉无尽的黑暗,无言地笼罩着整个辽阔的非洲草原,无声处是寂静,淡漠处又是无言.那么广袤的天,看得她眼睛都痛了. 她努力辨认着那些星座,姐姐从前喜欢星象占卜,总是对她提起,而她总说,姐姐拜托,我怎么会信那个. 投身科学的人,总是喜欢凡事有个前因后果,最好再来个环环相扣什么的,好像这样才显得出渺小人类对于自然界的征服欲与存在感.对于那些星象手纹之流,从来不信. 而她现在,望着南方天空最闪亮的一颗星,多想有人像姐姐一样,为她讲述它来自何方,又代表些什么. 可她的身旁,空了好多年. 其实也无所谓的.她闭上眼,想到. 耳边只剩下空旷的风声和破碎的音符,她似乎快要沉沉睡去,她希望梦境是一方温暖的湖,恬淡平静,而不要像一座寒冷的冰窖,压得她发不出声音. 黑夜降临的更多,将她围住,然后与尘世隔离.青草的味道在周围环绕,其实也不比夏奈尔的香水差. 她抿起嘴角,有些无赖的想,我就一辈子留在这里好了.她爱广阔草原上金黄色的落日,她爱深蓝苍穹上的闪烁星空,她爱旱季时空气中的草料气味,她爱雨季后天边悬着的那一弯明丽彩虹. 她不会走. 她不去巴黎不去米兰不去布拉格也不去伦敦,她也可以不要Dior不要Chanel不要Prada什么也不要,她就想在这里守着那些装着消毒水麻醉剂的瓶瓶罐罐,安宁地生活. 再也不离开. 她眯起那双冰蓝色的漂亮的眼睛,轻声笑了. 兰和人们手拉手围成圈子跳舞,不时用余光悄悄的看一下独自坐在外面的工藤.他没有加入进来,就一直坐在那里,不动,也不说话,就是那么静静的坐着,像一棵静默的树. 他怎么了? 兰的困惑想藤蔓一样在心里缠绕盘旋着生根滋长,她想问他很久了,可是即使不问,她也想得到他肯定不会说.她远远地看着他,觉得他不再是那个和自己一起长大的俊朗的少年,不再是那个笑容里写满自信的侦探,他越走越远,她都不认识他了. 那个什么黑衣组织,那种奇怪的药,还有那个面容清秀冷然的灰原哀,究竟改变了他什么?她一点也不明白. 她不明白他怎么会不远千里跑到这里来,她不明白下午订机票时他眼睛中复杂的神情,她不明白明明是她拥有着他独一无二的温暖笑容可那笑里的味道却让她陌生,她不明白为何他们的距离会变得遥远... 她不明白. 可她知道,这些日子里,他所牵挂的人,一直是她. 是那个有着一双美丽至极的冰蓝色眸子的她,是那个即使穿着普通的医生的白大褂也会显得超凡脱俗,十分高贵的她,是那个不苟言笑,被这里的人们当作女神来敬爱的她,灰原哀.而不是她,不是. 她的心里像是裂开了巨大的深渊,空洞而痛苦. 她看见那个和灰原很要好的叫做井上的护士走到新一身边,低下头对他说了些什么. 他摇头,隔得太远,他脸上的表情太模糊. 井上也摇了摇头,然后他站了起来,拨开人群,跑开了. "新一..."她的声音被淹没在了喧闹中,什么也没有留下. 她的眼中突然噙满了泪水.他那么匆忙的跑远,就像多年前,他们曾经是高中生时,一模一样.她留不住,也跟不上,她永远就只能站在原地看着他远去的背影,任凭泪水一次又一次的划过脸庞. 究竟是幸福太遥远,还是她的步调太缓慢,总是差了那么一拍,就再也合不上. 她去哪里了?他有些没头绪,那家伙,总是这样,说不见就不见,一点痕迹也不留。 所以,当他气喘吁吁的在那个山坡上看见她悠闲地躺在那里时,气得真想把她揪起来扔出去。 她听到身后的脚步声,微微侧过头,轻声问:“工藤?” “除了我还有谁?”他在她身旁坐下,“谁还有心有力找你这个大麻烦。” 她斜斜的扫了他一眼,懒得搭理他。 “我明天就走了。” “我知道。”她闭着眼睛,回答。 “你呢。”他轻声问了一句,却是陈述的语气。 “我?”她反问,“我不走。”语气是清淡的,却像是有点毒气的意思在里面。 “我就知道。”他说,“我知道你才不会走,这里是多么大的动物园啊……” 她笑了,说唉怎么被你知道了呢。 他既然能千里迢迢的飞到这里来,就说明了他无比坚定的决心,想要她回去。回到东京,回到米花,回到那个他们都熟悉的地方,安定的生活。 他也有天真的时候,那个想法就是证据。 可他错了。 他记得在她告诉他解药做成功的前一天,她一个人,在早上无声的出门,把好些地方重新走了一遍。而她不知道的是,他一直跟在她的身后,如影子样,整整一天。 看她走过他们踢过足球的公园,走过他们看过演唱会的武道馆,走过他们看过球赛的体育场,走过他们吃过寿司的饭店,走过他们上下学必经的那条熟悉的街。 晨光变换成落日,霞光披散,普照人间。 她走过一片又一片的风景,最后走进了帝丹小学,那个给了她一个机会还她缺失童年的地方。 他无声的看着她,看着她细细地看过学校内的一草一木,看着她缓缓地走过他们的操场,看着她轻轻地碰触老枫树干枯的树皮,美好如同精灵一样的女孩子,望着东京上空血红的黄昏,久久无言。 那是她在东京渡过的,最后几个夜晚。 他追随的目光变得疼痛,他心里痛极了。 他从来都不知道,原来表面上对什么都不在乎的她,会如此珍惜。珍惜这些平凡年岁里的微小幸福,珍惜他们五人之间细细碎碎的点滴回忆。 原来她如此珍惜。 当时的他想要告诉她,你的生活不久就会有全新的开始,可他没想到,他的话还没有说出口,她就拎着简单的行李,消失得一干二净。 他记得当时步美伤心的泪水,博士难过的表情,还有自己难以言状的恼怒。 如果简短的告别就说明了一切,那么人类长久以来进化出的语言是干什么的! 如果离开就解决了问题,那世界不早就乱成了一锅粥,人人不都成了逃亡者! 他真是对她没辙了。 所以他才一放暑假,就丢下案件足球,迫不及待的飞去了乌干达。他想在她那里得到确认,虽说眼见不一定为实,但总会比耳听来的利索。 但每每对上她那双清冷如同蓝宝石一样的眼睛,他总会哑然。 可在这一个多月里,他总算明白了她的执着。 她脚下的广阔的非洲高原的土地,从泛泛红海沿东非大裂谷,洋洋洒洒的延伸到好望角,每一寸原始的土壤都值得让她的灵魂为之燃烧。明明拥有无比古老的文明与历史,却在几百年来饱受人类工业文明的恶果--殖民扩张的折磨,东非高原的血红夕阳,蕴含了多少奴隶的耻辱与血泪,谁又数得清道得尽。她向来都是善良的人,可又无法改变什么,于是,她留在这里,一点点的努力,一点点的重新来过。 他明白她了。 她的心像是维多利亚湖的湖水,波光潋滟,清凌凌的一片。 那么,他尊重她留在这里的选择。 他终于解开了心中的疑惑,尘埃落定,水落石出。 他回东京读他的大学当他的侦探,她在这里诊她的病人做她的医生。 是不是就此远离? 不,不会,不会的。 因为,他已经知道,那个他无论如何都不想远离的心灵,就在这里。 “回去以后,好好照顾博士。”她说道。 “我知道,你平时也多给他打电话,他最想的不还是你。”他回答道。 她浅笑,“我知道,也会打的。”说完从口袋里拿出一挂手串,递给他。 “什么?”他接了过去,就着月光,隐约看得到上面精致的手工刻纹。 “好像是这里的一种图腾,祝福吉祥如意的吧,别人给我的。”她说着,“回去带给博士,不许私吞。” “什么嘛,我还以为是给我的呢。”他撇撇嘴,装出一副不满的神情。 “得了吧。少来。”她淡淡的扫了他一眼。 他没再说话,山顶上重归寂静。 山下的喧闹声清晰可闻,欢快的乐声没有停顿,祝福明日远行的人,一路平安。 “哎,工藤,你怎么跑来找我了。”女子突然发问,声音淡淡的。 “井上问我有没有看见你,我就知道你这家伙又不知道一个人跑到哪去了。”他有些闷闷地回应。 “怎么了。”她回过头直视着他,“你知道我问的是什么。” “你也知道我想问的,不是么?”他冲她调皮地眨了眨眼睛,一下子好像变成了那个熟悉又陌生的小学生,带着假装出来的天真笑容,一脸纯净。 他们总是这样,能先一步了解对方的思想,不多言语,亦是知晓。他们也总能从对方的眼里看出时间的变迁,岁月的痕迹。 女子叹口气,从草地上起来坐好,说道:“你想要的答案,你比我更清楚。” 你不就是想确认确认什么我过得好不好么,这些日子你不都也看着呢么吗,那你还要我给你解释什么,还是非得要我亲口说些什么你才会相信吗。 相信那个她要一直留在这里的事实。 是侦探也不能这样吧,反反复复你以为你验尸呢。 “灰原,在学校的时候,我从图书馆里看到这么一句话。”他的声音慢慢地低沉了下去,像波尔多出产的上好葡萄酒,不知不觉,已是沉醉。 “什么话?”她问道,心想肯定是哪本年代久远的推理小说里的台词吧。 “除非到了临别的时候,爱永远不会知道自己的深浅。”他说道。 她心里猛地一惊,不曾想他怎么会用到这样的词句,却仍然微笑着说:“哟,大侦探也看《先知》么。” 他不回答,只是继续往下说:“爱除自身外无施与,除自身外无接受---” “爱不据有,也不被据有。因为爱在爱中满足了。”女子接着他的话说了下去,淡定而自然的,说了下去。 他们都没有再说话。这时的夜,越来越深,月色如水,灼灼其华。山下的乐声渐渐的停止了,风也渐渐的冷了起来,他脱下他的外套,递给她。 她也不言谢,只是平静的接过去,披在身上。 “工藤,回去吧。‘她率先站起身,对他伸出手,手指在月光下显得更加的苍白而修长,却不失力度。 他径直站了起来,不着痕迹的揽她入怀,山顶上除了风声,一切寂静。 如果心跳不是人的本能,她想自己现在的血液循环怕是要停了。 他只是轻轻地环着她,像对待一件易碎的珍宝,不再言语。她只是勾了勾漂亮的唇线,将下巴抵在他的肩头。 标准的离别式拥抱。 半晌,她轻声说:“工藤,再见。” 是,再见。 这一去隔了千山,跨了万水,天知道下一次要什么时候才见得到她。就算是朋友之间的别离,也不会因此而显得过分,而他们却是最重要的同伴,对,就是同伴,那还是他下的定义。 那就让一切顺理成章地继续好了。 他们是同伴,是最重要的朋友。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hthaituna.com/htwxtz/7565.html
- 上一篇文章: 海豚老夏感谢祖国和时代,我愿意做中国的阿
- 下一篇文章: 用一句话概况ldquo海豚嘴rd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