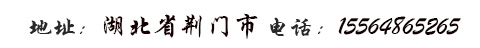那一湾海豚染红的泪焦点
|
楔子 海浪浸润着皮肤,溅起的泡沫如点点萤火。远处朦胧的陆影从薄雾里冒出来。 一群海豚们自由游泳。我的背鳍沐浴着阳光。躯体在水面跃起弧线,像雨滴一般陨落,隐在粼粼的涟漪里。心中甜蜜的躁动:“一定……不,似乎……就快见到他了吧。唉,阔别七年多了——山本,山本,”思绪浓烈了,“你……还会好么? 蓝·记忆 往事像无忧的大海,在碧绿群山间漫溯。太地町,这个美丽的故乡,有着生灵、土壤、海湾,神庙风铃的清响和祈福……听说居民们喜欢海豚和鲸,连路牌都是这些图案呢。女孩子淡雅如樱花,男孩子则皮肤黝黑又和善,譬如山本。他曾是我幼年的玩伴,瘦弱,小眯缝眼,一笑便露出泛黄的龅牙。我们经常一起戏水玩耍。海风中他抛皮球,我便用宽吻顶回来;或者在雪浪里捉迷藏,礁石成了精致伪装……我俩都外表如“上帝弃婴”:一岁时我贪玩撞到渔船铁锚,鳍上便有三道疤痕;而山本脖上有紫青的胎记。 “想些什么呢?心不在焉的。”同行的海豚长者问。“哦,没什么,一些遥远的事罢了。”我们向层叠的山峰游近。 海豚和人类社会有诸多相似之处,群居,思考,有一套自己的语言——喉咙里的声浪。但小山本的心却有灵犀读懂。当黄昏的黯淡余晖散落在海滩,他便凝视着耄耋夕阳,海天是那么壮阔的暖色,两三只白鸥点缀着霞光。他时而手垂在腰后,踱步着喃喃自语:“多美的红色,多美的海湾啊!”我游近,他便抚摸我水蓝的前额,向我倾诉故事,并感叹:“哦,‘三道疤’!时光多美!”我回应以幸福的声波,汇报最近逮到几条鲅鱼或乌贼,他便点头笑了。 我自诩是山本的守护神,因曾救过他命。我们初识,是他在十三岁溺水那次,我还是海豚幼崽。岸上渔民孩子挑衅的声音又清晰:“紫脖子,你有种游远些看呀!?”“瞧!胆小鬼,怕了吧!!”山本耸着肩,脸窘得通红。半晌,我和母亲驮着呛水到面色苍白的他靠岸。他虚弱地眯起小眼睛,挤出一丝惨淡笑容,用手轻抚我背鳍上的疮疤:“小海豚……伤……还痛吗?” 我不知“三道疤”留下怎样的记忆。或许永远烙印在他脑海里,闪烁像深蓝海水里的光斑;又或许,只浅浅地随风散了呢?我疑惑——难道上帝给我独特的疤痕,是神秘的契约么? 唉,七年了…… 灰·离殇 我背井离乡了七年。这一湾峻秀山水,曾是我回忆的禁地。 七年前我作为外来者加入这个串本町的群体。十二只海豚很友善,教会我捕鱼、夜航、警惕鲨鱼等技能。快八十岁的雄海豚信智是首领。现在,几位年轻的猎鱼手和他有了路线分歧:如鲸、苍鲨等坚持反对靠近未知海滩,但信智却袒护我的意愿:“我们再往岸边看看吧,毕竟,那是慧子的故乡啊。” 傍晚山峰是一峦峦青黛影,露珠弥漫在阴湿空气里。海水蜿蜒如银蛇,最终隐没山间。我们游去。这是七年前母亲与其他亲友消逝的地方。我的神经隐隐刺痛着。 “你一定想起了一些故事吧?”我缄默不语。 时光里那一阵阵噪声又冲入脑海。三岁的我还喜欢倚在母亲白肚皮上撒娇。那个宁静的傍晚,火烧云如油彩嵌在天际。太地町海豚群被渔船包围了。首领觉得这是个误会,或许是我们捕食鱼类干扰了渔民生意?很快的,男人们拼命敲打起钢铁长杆,“咚——咚——”的巨响霹雳一般袭来。海豚对声音极为敏感和依赖。金属轰鸣被海浪搅碎了,欲震裂耳膜。瞬间世界昏暗起来,无法沟通和辨识方向,惨叫声像疟疾一样蔓延开。我紧紧依偎着母亲的胸鳍,她的眼哀伤而慈爱。几秒之后,渔船彻底冲散海豚群,男子们的吆喊和钢铁声钻入骨髓。天地依旧壮美的红,海水在静静呜咽。骤然,一只渔船撞散我和母亲,“妈妈——”我吓哭了。“慧子,快逃——快离开!!”我嚎叫着穿过无数渔船,拼命地向深海游去,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理睬。寒浪像刀子一般割痛心脏。渐渐的,海面沉静了下来,唯有紫霞与残晖,摇曳在细澜里,如美人半遮面的红绸…… 而今这诀别的山峰就在眼前,我不禁驻足。“怎么了慧子?”信智问,“你不是很想回乡的吗?”“啊,啊,没错。”如鲸摇晃着庞大的尾巴游过来,有些粗哼:“慧子,你这样犹豫,难道前面有什么危险嘛?”“没,只是……”“我看她是太想家了,现在到了反而傻傻的,不知所措了。”信智轻松地微笑。 七年前,孤零零的我要离开这冷寂故乡。让梦,美好的歹邪的,都随海风飘散吧。我不解:真是我们捕食了过多海鱼理应受罚么?如果是渔民和海豚间一场误会,时间会澄清。——又或许,那些爱海豚的渔民们把母亲他们带到更富饶的海域生活了呢? 我走前不忘向小山本告别。橙红的黄昏,他驻立在海滩。群山被染成墨绿色,泛着寺庙中枯山水般祥和的光芒。海水一圈圈涟漪,像少女和服的裙裾。“三道疤!”晚风吹拂着白布衫,他眼中荡漾起惊喜,跳起来招手。我把前额浮出水面,在不远处静静地望着他:瘦削的身材,短黑发,古铜色脸庞上眯成月牙的小眼睛,龅牙,脖上的胎记,和被夕阳拉长的灰影子……我向他致意。“海豚的微笑,多美啊!”他兴奋呼喊。骊歌无声地奏响。我含着腹泪,纵深跃入波浪里,游远。 我知道终有一天要回来。心底的好多话要向他讲。关于母亲、太地町海豚、往事和故土。 山本一定知道答案吧。 红·海湾 公元历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日,串本町海豚群的故事结束在这个海湾。 天色阴暗下来,我们正打算寻找礁石滩歇息,明早启程别处。忽然山谷间,我看到一艘小渔船上有瘦弱的男人身影。定睛打量,呼吸渐渐急促:“真的是他?……啊,不会看错吧?” 我飞速向那艘船游水。“慧子!”苍鲨叫住我。海豚从不分开行动,信智示意大家凑近。那男人似乎注意到什么,挥一挥手,驶船入山涧。海水凉浸浸的,夜幕缓缓吞没树影。一瞬间我嗅到往昔的味道,卖力地游着,有种错觉:山本会带我找到母亲。 可是当在那个半封闭的海湾里回身已晚时,七年前的梦魇又重演。渔船星罗棋布地包抄,熟悉的钢杆噪声带来钻心疼痛,海豚们似溃军般逃窜、惨叫、哀嚎,而后被驱赶到一个我陌生的石岸边。十三只海豚都受了惊吓,年迈的义和有些奄奄一息,几只雄海豚愤慨地埋怨首领带错路线。黑夜笼罩,天上没有一颗星星。渔灯和密网封锁成囹圄。所有海豚都忧心忡忡,无比的自责和罪恶感涌上我心头——难道我本不该回故乡么?次日黎明,如鲸等几只强壮的雄性宽吻海豚被一些海洋馆的人掳走了。渔民们目光矍铄地一遍遍数着纸钞,咧嘴大笑着畅谈。船上那个清瘦的男人却始终不见。 当清晨露气在水面氤氲,旭日从海天一线的远方攀上来。云彩淡红而温柔,水波上光斑跳跃,像晶莹的泪珠。静悄悄地,静悄悄地,一场血色的大屠杀降临了。 靠岸的玲子最先被残害。一个膀大腰圆的渔夫用长枪刺向她水蓝色的身体。她凄惨的尖叫声波在海湾回荡,光滑的背部绽放出一纹猩红血痕,像漆夜里的艳丽烟花。渔夫嘶吼着拔出枪,又举高猛地刺下。玲子拼命挣扎着。雪白的腹部被击穿,红色鲜血随水波泛开。剧痛使她的哭泣声响彻云霄,伴着另八只海豚惊恐的和鸣。她踉跄着企图逃窜,却被船只赶上又是一枪。累累伤痕漫上她秀美的流线型躯体,宛如钢刀任情飞舞于白壁。她猛然跃起,溅起红的水花,又重重摔下来,尾鳍疯狂地颤抖着。突然,她瞪大眼睛安静了。之后永远地浮起,似一瓣玫瑰轻漂在小溪水上。原本三月后她便可第一次分娩小海豚啊!渔民们大笑喝彩——海豚肉即是钱财。时间死寂了一般。 屠杀的死神召唤着每一只海豚。渔船们蜂拥而至,长枪刺向八个曾在湛蓝海洋里自由游水的生灵。阳光镀着泛红的海水。红色,太地町海湾到处都是红色!红的海豚,红的波纹,红的渔民的手和衣裤。深黛峰峦间,风依旧无忧地来去,时而吹拂着海豚们绽开的背脊,血肉模糊的胸鳍,和暴露的颅骨,飘走那绝望的哀怨,哀怨的绝望。我满是伤痕,轻微喘息地抽搐着。海水的红斑连成大片,浅红的波澜变作暗红,红色慢慢吞噬了大海远方的边界…… 一切都安静了。山间小路上,朦胧传来一位少女的清歌:“樱花啊,樱花啊,阳春三月晴空下……”清早的海湾静了。 尾声 我不愿再挣扎。恍惚间,汗毛耸立起来。 “紫脖子,收大鱼了!”“懦夫,看看你才干掉几只!”船上那个瘦弱男人的身影踱来踱去。他佝偻着背,抬头看云。手上有根暗红的破长枪。我的心颤动着。 终于他目光锁住我滴血的背鳍。小眯缝眼快要崩出眼眶,嘴巴张得巨大。他飞奔来抚摸那三道疤,痴呆了一般;“啊……这是……啊……”或许他想到了多少年前壮美的橘红色黄昏?海滩旁的捉迷藏游戏?那次溺水?抑或…… “扑通”一声,他像山崩一样跪倒。把头俯在我背上久久地哭嚎。 他辜负了朋友。红色海湾畔,他卑微似一簇浪花。 写在后面 阅此文章的短短几分钟,杀戮仍继续在太地町的海湾。这是一篇基于奥斯卡金像奖影片《海豚湾》()而创作的小说。每年9月至次年3月,约2.3万只海豚在日本被“合法”捕杀。太地町成千上万只海豚被渔民驱赶至石滩,一些幸运的宽吻海豚被海洋馆以15万美金的价格购入表演,其余则惨遭屠杀,用以肉食贩卖。海水一度被染成触目惊心的腥红色。面对国际海洋动物保护协会等世界舆论谴责,日本政府坚称捕杀海豚为当地传统,甚至将小型鱼类数量减少原因极大归咎于海豚捕食,而非过度捕捞,漠视吨含汞极度超标的海豚肉流入食品市场。可是,本不适宜时代的“传统”不应是残忍屠害“蓝色精灵”的借口,血腥杀戮成群海豚的行为亦与人道主义背道而驰。无数的“海豚湾”应被加大曝光和逐渐摒弃,以归还海洋的和谐生态系统和宁静祥和景象。公益组织亦应为此呼声,通过舆论为猎豚行动施加道德压力,让那一湾湾海水不再是催人泪下的暗红色,而是海豚自由栖息繁衍的湛蓝天堂。 扶葭 来自香港大学与香港中文大学的学生公益团队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hthaituna.com/htfzfs/1546.html
- 上一篇文章: 榴岛视角不负自然禀赋深化玉环渔业品
- 下一篇文章: 一年四季,在葡萄牙乐享不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