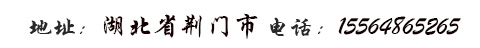李存荣
|
读《风雅颂齿韵》有感文 医院(医院)李存荣 作者简介:李存荣,副主任医师,副教授,现任国家卫健委全国儿童口腔预防保健项目专家委员会顾问。原任中华口腔医学会预防口腔医学专委会常委、中华预防医学会口腔卫生保健专委会常委、上海市口腔医学会口腔预防医学专委会副主任委员、上海市预防医学会口腔预防保健专委会常委、医院(医院)口腔预防处处长、上海交通大学口腔医学院客座副教授。长期从事口腔预防医学、口腔公共卫生和项目管理的实践与研究,擅长口腔健康个性化设计和监护、口气诊疗、龋病和牙周疾病预防诊疗适宜技术。参与编写《口腔卫生保健丛书》、《现代口腔社会医学论坛》、《儿童青少年卫生学》、《口腔公共卫生》等多部专业书籍,参与国家和主持上海口腔卫生研究和调研项目10多项。 我荣幸地拜读了卞金有教授编著的《风雅颂齿韵》大著。一位耄耋医者以一己之力搭建“忠贞口齿人文书院”平台,并以此文作为开启之金钥匙,意在遵循祖训,秉承质疑、问难、辩论之精神,探讨口腔健康科学人文之源,发掘中华口齿人文脉络之瑰宝,与世界多元文化中口齿人文之印迹。切问而近思,发出唯有此“才能促使口齿人文素养知行合一之形成,促进口腔健康与全身健康之提升,生命质量之提高”的呼喊。诚如他的挚友张永鑫教授所言,他是一位“知者似水达理而周流不滞,仁者如山安义而厚重不迁”的学者。我感慨卞教授在耄耋之年,依然不忘初心,花了10年功夫,把散落的无人问津的伤感齿诗汇聚成这部大著,实在是令人敬佩。中学时代我就喜欢诗词歌赋,现在读到这本荟萃历代文人雅士的“齿诗”既被震撼到了,又感到一种巨大的无奈心情,随之也引发了一些思考。 《风雅颂齿韵》是一部千年历代文人雅士的齿诗荟萃,吟唱了饱受牙病苦痛的齿殇之歌。在诗人眼里,“齿落”恰如珍珠坠入玉盘,还伴随着叮叮当当的韵律,好凄美呀!在民众心中却是“牙疼不是病,疼起来真要命”,也绝不是一件开心浪漫的事。大量的古代传统医学文献也表明,古人对口腔医疗卫生保健是极为重视的,一度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千年悖论现象,鉴赏古人“齿诗”又有什么现实意义呢?可否从以下二条线的角度去鉴赏与思考: 先秦汉魏、唐宋元明清等历朝历代,大约有多位大诗人,几乎一生都饱受牙病的痛苦折磨,留下了多首齿诗,吟唱了饱受牙病苦痛的齿殇之歌。尤其是南宋大诗人陆游,在他85年的生命中竟有40多年牙病苦难史,“甘寒虽遶齿”(牙齿过敏),“齿根浮动叹吾衰”(牙齿松动),“耄齿觉衰蹉已晚”(牙齿已无法挽回),齿痛的体验撞击了他的心灵,书写出了首吟脍炙人口吟诵齿痛的诗篇。 公元前年的《礼记》就有记载口齿人文的名言警句,如“鸡初鸣咸盥漱”,就是每天鸡叫头遍,起床后用盐水漱口,最早把清洁口腔作为家庭礼数的一种基本礼仪。在认识口腔疾病方面:《黄帝内经》中对龋病、牙周病、口唇病、口疮、口糜等疾病都有论述,认为口腔器官病变与脏腑功能失调,气血盛衰有必然联系,也就是口腔疾病与全身健康关系密切,这种观点至今看来仍具有先见性。汉代张仲景《金匮要略》中有两处涉及口齿病症,其一“狐惑病”(现代称为眼、口、生殖器综合症);其二“小儿疳虫蚀齿方”中的雄黄是含砷的失活剂,西方要到年才开始用含砷的失活剂。魏晋时期嵇康《养生论》中记载有“齿居晋而黄”,他观察到山西有些地方的人牙齿是黄的(氟斑牙),是最早记载氟斑牙的人。唐代孙思邈《千金要方》其中涉略口病、舌病、唇病、齿病、面药五个方面内容,都与现代口腔颌面部疾病有关;唐代王焘《外台秘要方》就有牙结石的详细记载,对龈上和龈下牙结石都已有了明确的认识,并能施行“钳刀”器具剔除牙结石的疗法。宋代王怀隐《太平圣惠方(口齿论)》,尤其对龋齿、牙周疾病的发生、临床症状及治疗方法有了高度认识。在口腔卫生保健用品方面:《礼记》也有“毋刺齿”的描述,这是我国最早的“剔牙”文字的描述,年在洛阳古墓出土的8枚骨质牙签实物,证明了年前古人就有剔牙的习俗了,此后在汉代、唐宋明清文献中都有“牙签”的记载。南北朝梁代刘峻《类苑》中首见对牙粉研究的记载,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早的药物牙粉。宋代苏轼《东坡杂记》中谈到的饮茶及漱口防龋方法,现代科学证明,茶叶中的氟和茶多酚具有防龋固齿的作用。我国考古实物见证,唐宋年间(迄今多年)就有了植毛牙刷,比欧洲年才出现牙刷要早了多年。牙刷、牙粉、牙签、饮茶的发明、发现和使用的史料,表明从古时候起就开启重视口腔卫生保健的历史进程,体现了中华文明对人类口腔健康的重大贡献。 如上所述,产生了一个令我感到困惑的问题。按理说先秦汉魏、唐宋元明清各个朝代的文人雅士,完全有机会接触到这些古医书和文献的,寻求医治牙病和采取自我口腔保健措施也是不怎么困难的,但事实上都基本采取了隐忍牙痛之苦的态度,有感而发地写下了“齿暮”之歌,以表达乐观面对现实,自我安慰,从中寻找乐趣的豪放精神。 直至当今社会生活中隐忍“牙疼不是病,疼起来真要命”现象也是屡见不鲜,“小孩牙齿反正要换,坏了不补也没有关系”、“老了掉牙齿是正常的,牙齿太好要嚼子孙的”等说法在民间还是流传很广。还记得那些年的全国爱牙日活动,有些省市利用教师节特别设置“教师免费服务卡”,结果能持卡按时接受服务的教师却是很少。20世纪90年代末,我参加了一次全国牙病防治指导组在山东曲阜举办的会议活动,期间我询问与会的孔子七十二代孙,“孔子是我国古代儒家学派创始人,修《诗》、《书》,定《礼》、《乐》,序《周易》,作《春秋》。他的儒家思想及学说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也被历代君王尊崇,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脉,深刻影响到中华民族的民风民俗的形成和传承。他老人家有没有对牙齿卫生保健也有一些论述?”,这位七十二代孙回答说,“也真被你问倒了,我家老祖宗面部七瘘,齿瘘、耳瘘、鼻瘘……,个人卫生是不好的”(这段话至今我印象深刻)。我心想,老祖宗都没把牙病当回事,“齿文化”也没能被历代君王所推崇,缺少传统文化基因的影响,依旧是“小众”文化,那些达官贵人、文人雅士也是深受齿痛之苦而隐忍,“牙痛不是病”习俗流传至今未绝。 自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全国牙防指导组成立(至7年4月撤销)以来,我国始终把口腔健康教育活动作为重要的抓手,利用多种媒体加强对民众的口腔健康教育普及力度,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遇到难以深入的瓶颈问题。相关调查表明,一方面民众是对口腔卫生保健知识传播持欢迎和急切的态度,另一方面又往往以很快的速度被遗忘,能够真正努力践行改变自己行为的并不乐观,能够传承下一代就更是少之又少。该如何改变此种现象?我想,一个重要的检视角度,就是特别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hthaituna.com/htqxhj/10619.html
- 上一篇文章: 云bull共享ldquo童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