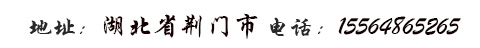侯凌肖远去的炊烟齐鲁壹点
|
文 侯凌肖编辑 燕子图片 网络黎明,我骑着变速车去乡间小路转了一圈。清晨是安静的,远处偶尔转来几声鸡啼狗吠声。向晨曦中苏醒的村庄望去,只见村庄的上空升腾起袅袅炊烟,吸一口醇香的烟火味,一种相思油然而生,勾起的往事陈年老酒一样醇香醉人。炊烟是乡村的符号,炊烟记载着我家乡人一天的幸福与快乐,炊烟是农村人在农村版图上的日记。炊烟是母亲发给儿女的信号,远远地只要看到家中小屋冒出的炊烟,说明母亲已经开始烧火做饭了。再贪玩回家去晚了的话,唯恐又要挨骂了罢。故乡四季轮回、寒暑易序的岁月中,时常变换着田间地头的庄稼和河边的花草,不变的是盘桓在青瓦上温馨而醇香的炊烟,以及伫立在一炷炷炊烟背景中的母亲。炊烟记载着母亲作为“家庭主妇”的尽职尽责。母亲的身上,聚集浓缩着农村女性辛劳隐忍的身影,难道不是吗?当蘸着朝霞的鸡鸣声响彻村庄时,母亲便踏着第一缕晨曦,开始了锅碗瓢盆的人间交响。绽放于乡村帽沿上的炊烟,是父母亲用颗粒饱满的汗珠浇灌出的风吹不折、雨淋不湿的庄稼。只要看到炊烟,我的灵魂就会回到故乡,回到生我养我的母亲身旁。记忆中的炊烟,漫过低矮泥墙农舍,漫过错落相间的树林,如蝉翼般轻柔地荡漾在村庄周围的村寨土岗上,给落寞的村庄营造了一派朦胧色彩。童年时,无论玩得多久,跑得多远,到吃饭时,朝着炊烟袅袅的方向,回到家里。推开那虚掩的大门,在庭院深处的老梨树下,有一张小方桌,桌上香味扑鼻的饭菜正“诱惑着我的味蕾……生活艰难的岁月里,粮食不够吃,母亲常提着竹篮,到田间地头采撷各种野菜,拌着黄灿灿玉米面,做几顿新鲜的菜粥。有榆树钱时,村寨土岗上有母亲采摘嫩绿榆钱的身影,中午时分,饥饿的我会品尝到榆树钱窝窝头的香甜。待到4一5月份,也是北方一簇簇槐花盛开的时候,母亲提上竹篮、拿上绑着镰刀的竹竿,乐颠颠地去往村寨土岗,采摘些香甜洁白的槐花,掺合面粉做些槐花饼子吃。那时的冬天格外的冷,土屋里冷得如冰窖。小时候十分贪恋被窝的余温,迟迟不肯起床。早晨的阳光透过方格的门亮窗斜照在被子上,厨屋里的风箱“啪嗒”声和烟火气,一同从门窗缝里“挤”进来。“坐起来,吃点红薯轱轮吧!”母亲从厨屋里端出一碗热腾腾的红薯,耐心地做着我起床的“工作”。母亲接着说:“冻得都是懒人!快起來帮我烧锅吧,锅门前暖和。”老屋破陋不堪,四处透风,想到锅门前能取暖,于是,我麻利地穿上棉衣,逃避似地跑出了土屋。母亲总是用炊烟温暖了艰难的岁月,把平淡凄苦的日子过得暖洋洋、乐融融。记得我上魏庄大队完小时,每天天还没亮,母亲就忙碌起来,生火、烧水、做饭,唯恐我放学后不能及时吃上饭,当邻家的炊烟开始升起的时候,我早已兴致勃勃地走在上学的路上了。薄暮时分,母亲常站在村头张望,一瞅见我的影子,就快步返回家中,在灶间拉风箱、添柴禾,温热那已经放凉的饭菜。于是,炊烟袅袅升腾,弥漫在寂静的夜空。有时厨屋柴草潮湿时,点燃就很费母亲功夫,一个劲地往外冒时,劳作在烟雾中的母亲往往被呛得咳嗽连连,眼泪不住地流,常常整得灰头灰脸。那时,我不太明白什么是伟大的母爱。在母亲的关怀和爱抚下,我的身体健康结实,学习在班里总是名列前茅,那一张张学校发的奖状,就是最好的证明。年8月6日,是我离开故乡,到建筑公司“接班”报道的日子。勤劳的母亲一大早就在厨屋里忙着为我做早饭。风箱的“啪嗒”声把我从睡梦中吵醒。我急忙起床从西屋里走出来,只见东屋(厨房)房顶烟囱炊烟袅袅,厨屋里缭绕的烟雾下,苍老的母亲正坐在灶旁,一手拉着风箱,一手往灶堂里填柴,灶堂里的火苗一闪一闪地映红了母亲布满皱纹的脸庞。一股暖流瞬间涌遍我的全身,双眼已朦胧。母亲佝偻着身子为我做饭的那一幕,永远烙印在我记忆的底片上。“可怜天下父母心”。临走时,母亲从水瓢中拿出早已煮好的6个鸡蛋,硬是塞进我的挎包,:嘱咐我路上饿了好充饥。想到生活节俭、平时都不舍得吃的母亲,我心头掠过一阵酸楚和心痛。真是“儿行千里母担忧”啊!我紧紧握住母亲枯瘦的双手激动地说:“娘,您保重身体,我会常来看您的!”年9月16日,母亲病逝在故乡的老宅院中,俺兄弟三人悲痛欲绝……时光如流水。慈母已去世多年,那温馨的袅袅炊烟也早已远去,但对慈母深深的缅怀和思念,至今却时常萦绕在我的心头。作者简介:侯凌肖,山东鄄城人。现在山东金润建设有限公司工作,高级工程师,山东散文学会会员。散文作品散见于《齐鲁晚报》、今日菏泽《风雅颂》、辽宁《刊授党校》、《职工天地》、《山东建筑业》、《山东建设报》、《菏泽日报》、《牡丹晚报》等报刊壹点号心梦文学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hthaituna.com/htqxhj/13007.html
- 上一篇文章: 安家比起潘贵雨,我更讨厌房似锦的弟弟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