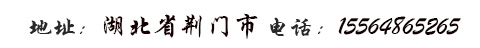贺昕我那巴掌大的小山村外三篇
|
我那巴掌大的小山村,像一只豁牙的破碗,盛得下我童年的所有欢乐,盛得下祖祖辈辈流淌在山山峁峁上的汗水,却盛不下一滴晶莹的泪珠。它就在我的心里滚啊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在凝神沉思的时候,在独步幽径的时候,从少年滚到中年。终于有一天,它涨落成肆意的潮水,满满地溢出来,漫过了尘世的喧嚣,漫过了快节奏奔走的步伐,最后,要淹没我那洁白的稿纸了。 学校是巴掌的纹理里一颗小小的痣,紧邻着的三个村的孩子们都在那里读书。请假是很随意的事,委托一个要好的孩子给老师说一声就行了。如果家长恰好在学校对面的山梁上挥舞着锄头劳作,就对着操场上散步的老师吼一嗓子:“噢——老师,我们家孩子请假了——”请多久,家长不说,老师也不问。请假对我来说也是家常便饭,上三年级时,我的父母干脆一劳永逸,给我请了两年半的长假。为什么请假?地里的庄稼像襁褓中哭泣的婴儿一声声揪扯着他们的心,而我那三个还没到上学年龄的弟弟急需要人照顾。十一岁的我义不容辞地当上了这个迷你幼儿园的园长。不久幼儿班又转来了新学生,隔壁大婶把她的小女儿委托给我,匆匆奔山里去了。 墙角移动的影子是时钟的指针,我每天按时给孩子们焖黄米粥,负责做一大家人的饭。十一口人的饭哪,我提起那口沉甸甸的大铁锅,就像一只瘦小的蚂蚁搬运一颗硕大的粮食。如果柴草潮湿,燃不着炭火,我就在滚滚浓烟中大声哭泣,下弦的月亮如果肯亲吻我的额头,那我一定是包公无疑了。我别出心裁地给孩子们改善伙食,却误将大婶送来的一碗荞面当成白面拌成了疙瘩汤,我们都吃得有滋有味,妈妈回来却好一顿责备,说孩子们迷迷瞪瞪的,都是荞面浆糊吃迷糊了脑子。我还会制作美味的零食,将沙土倒进热锅里,炒出香喷喷脆生生的豆豆。没事的时候我就带着孩子们咯嘣咯嘣地嚼着豆豆在大门口转悠。 大门口的那棵槐树开得热热闹闹的时候,地里的农活更忙了,大人们就像陀螺一样在地里团团转。寂静的小山村,似乎只听见我们嚼豆子的咯嘣咯嘣声,鸡鸣狗吠声,鸟儿的啁啾声,风吹树叶的沙沙声。出门见山,见山开花,对面山上的野菊花静静地开落,门口那满满的一树雪白袅袅低垂,似乎酝酿着一个甜蜜的梦。 一列队伍时不时打破小山村的宁静,他们风尘满面,步履疲惫。而牛驴似乎行走得更加艰难,它们的背上,大瓮套着小瓮,大盆套着小盆,形成沉甸甸的负荷。孩子们一看见远处山梁上移动的小黑点,就大声喊:“卖瓷的来了!”瓷器好啊,粮食装进去,老鼠咬不着,湿气潮不着,既保鲜又安全。他们卸下瓷器,坐在我家大门外的碾盘上招揽生意。饿了,拿起一个小瓷盆随便走入哪户人家,给女主人送上笑脸:“大娘,换一个窝头吧!” 而这一次,队伍里多了一张陌生的面孔,那是一张稚气未脱的脸,却像一片枯藤上的树叶。他背靠槐树坐着,脸上写满沮丧和忧郁。听人们议论,他的瓷器在半路上打碎了,连换窝头的小盆也没能幸免。我能感受到饥饿的利爪如何撕扯着他的心,因为我看到他的眼角包裹着一滴晶莹的泪珠。我开始憎恨拴在旁边的那头驴子,它肯定是欺负没有经验的主人,故意尥蹶子摔坏了瓷器。就像我们家的老黄牛和黑毛驴,大人们使唤时,它们一副温顺服帖的奴才相,我放牧时,它们就露出了放刁撒泼的本性。撒泡尿的功夫就偷啃庄稼,我下坡去赶牛,坡上又走了驴,我就在坡上和坡下展开了拉锯战,满头大汗,气喘吁吁。爸爸的责骂声像阵阵雷声从对面山梁上滚过来,庄稼主人的吆喝声又从另一座山头传来。鞭子的噼啪声给我的哭声伴奏,过路人也添油加醋:“嘿嘿,小毛孩,连牲口都欺负你!”现在,那头闯祸的驴子仰天长啸几声,它得意地笑呢! 也许,他太年轻,一心想证明给父母看,自己已经是家里独当一面的旗帜,想着赚了钞票给孩子买糖果,给妻子买漂亮的衣衫……他行色匆匆,甚至没来得及收拾好行囊。长途跋涉的艰辛以及路途上不可预知的困难都被美好的期待掩盖了。 现在,他茫然无助地坐在槐树下忍受着饥饿的折磨,却放不下自尊伸出乞讨的手,鼓不起勇气张开求索的唇。我和孩子们站成一排,悲悯地看着他,我手里的豆豆在口袋里攥出了汗水,却没有勇气给一个陌生人送上。就在这时,我那个最小的弟弟低头从口袋里往外掏,很快把小手伸了出去,掌心里滚动着几颗黄灿灿的豆豆。小伙子愣怔了一下,眼角那一大颗晶莹的泪珠瞬间飞珠溅玉般滚落下来,他用颤抖的大手接过小手里的豆豆,脸上紧绷的皮肤松弛开来,又弯下腰把我们撒落在泥土里的豆豆一颗一颗捡起来,嘴里念叨着:“看看,都撒地上了……” 四岁的弟弟就像一缕温暖的阳光,给那张枯叶般的脸重新点燃了春天,它精神抖擞了!满树冰清玉洁的槐花似乎也感受到了眼泪滚落时的震动,浓郁的香气氤氲了整个村庄。风儿醉了,癫狂地摇晃着满树银色的铃铛;枝头上的鸟儿醉了,一歪脑袋,吐出了一串亮丽的啾鸣;阳光醉了,将粉红的胭脂胡乱涂抹在我们脸上。 许多年过去了,那颗晶莹的泪珠一直在我心里滚动,他困顿的双脚将怎样翻越重重大山,回到日夜呼唤他的家园?小时候,常听大人们感叹:“出门人可怜哇!”然而,在茫茫的尘世里,又漂泊着多少个孤苦无依的灵魂?迷茫的心啊,希望有一缕风,能拂去你眼中的乌云;希望有一束光,能驱散你心底的黑暗;希望有一场甘霖,能滋润你干涸的心田。弟弟小手心里那几颗黄灿灿的豆豆又在我眼前滚动,世界有爱,一颗小小的豆豆也能孕育出绚丽的花朵,繁衍出一个花团锦簇,阳光明媚的春天。 寻找失落的乡愁 我站在故乡的土地上,目光掠过蓝天流云,掠过绿树飞鸟,掠过古老的窑洞,掠过故乡的每一寸肌肤,我在寻找,寻找曾经激荡着我童年欢声笑语的潺潺水流。 一看到那口老井,我的心就猛然抽搐了一下,笑意也凝固在了脸上。它就像一位皓首白须的老人,流淌着浑浊的泪滴,茫然地眺望着远山。没有鸟叫,没有蛙鸣,甚至连风都不愿在它旁边多停留片刻。偶尔,留守的老人拄着拐杖大声咳嗽着蹒跚而过,连头也不回一下。记忆的风从心头一阵阵吹过,曾经的老井前,是怎样一派车水马龙的繁忙景象呀! 天刚蒙蒙亮,挑水人就晃动着两只水桶,踏着有力的节奏,洒下一路吱吱扭扭的歌。鸟儿也醒了,在树梢上练嗓子。被井水滋养的树木格外葱茏,浓荫匝地。老井就像一位奶水充足的母亲,满满的井水溢出来,就像母亲洒落胸前的乳汁。再过一会儿,太阳爬上东面的山头,放牛的孩子提着水桶,拉着牛赶来了,牛一看见水,疯了似的挣脱了缰绳跑过去,扎下牛头对着井水猛吸几口。前来提水的老奶奶带着责备的口吻说:“看把牛渴成甚了!”小毛驴也来了,躺在旁边绵软的黄土地上,痛痛快快地打几个滚,站起来,抖抖尘土,打几个快意的响鼻。荷锄的来了,拉着牛车的来了,互相问候着,“今儿去哪儿锄地?”“你那块地赶紧锄吧,我昨天路过你那地,都快荒成草毯子了!”我们几个光屁股的小孩来了,在溢出的井水前筑一条堤坝,拾一片树叶放进去,就是大船了,忽然来一阵小风,那船便扬帆远航了,我们兴奋地欢呼着,撩拨着水花。 我们都不知道老井来多久了,打记事儿起它就戳在那儿了。只有老井清楚地记得,有多少乘花轿吹吹打打地从它身边抬过,有多少个小孩子像地里新种的秧苗一样,一茬一茬地冒出来,有多少只小鸟在它身旁的树杈里出窝。在它身旁走过鸡,跑过猫,路过的陌生人趴在井沿上咕咚咕咚地喝过水,大家都贪恋着那清凉爽口的井水哪! 忽然有一天,井水陷落下去了,连井底的石头都裸露出来,人们高高地撅起屁股,也打不上半桶水来,最后只能小心翼翼地踩着井壁的石缝下到井底,一瓢一瓢地舀水,井外还排着队哪!村民们议论纷纷,有的说老井附近的人家修窑洞打石头,隆隆的放炮声把石缝震裂,井水泄露到石缝里去了。有的说婆姨们在井边洗内裤,冲撞了水神……村里德高望重的老大爷张着没牙的嘴,蹲在井沿上,对着虚空缥缈的水神唱起了歌。他是祈雨队的领唱人,即兴改编的歌词套用了祈雨的调子,如泣如诉,大爷唱了三天,嗓子都嘶哑了,老井依然冷若冰霜,水神连一滴同情的泪都没有抛洒。 我沿着老井眺望的方向继续前行,脚下的这块平地,曾经是我家门前的小水沟,现在,它静静地沉睡在地下。然而,童年那梦幻般的小水沟就像发生在昨天的故事里。沟底金灿灿的油菜花在风中搔首弄姿,招蜂引蝶。瓜秧披挂着金黄的花朵多情地攀爬。追蝴蝶的孩子还站在油菜花丛中四处张望,咦,那两只黄蝴蝶飞哪去了?就像是昨天,那座小巧得两三步就能跨过去的石桥下面还流着清凌凌的水,一条小花蛇站在水里,冲着上学的孩子们吐舌头呢! 老井成了干瘪的乳房,小水沟就成了断奶的孩子,一天天消瘦,冬天来了,石崖上连水晶帘似的冰瀑布都挂不住了!有一天,一位老大爷探头看看沟底梧桐树上空荡荡的喜鹊窝说:“喜鹊怎么不见了?”是呀,好久听不见喜鹊在墙头叽叽喳喳地报喜了,它们和屋檐下的燕子一样,多么喜欢和庄户人家依偎在一起,好好地过日子。又过了数日,有人说:“狐狸哪去了?”哦,是好久不见狐狸的影子了!狐狸经常乘着夜色偷袭鸡窝,可是夜晚再也听不到鸡惊恐万状的呼救声了。年轻人说:“它们在这里喝不到水,搬到有水的地方去了!” 七夕的晚上,我躺在奶奶怀里听奶奶讲牛郎织女的故事,我仰望着夜空中那条白练似的银河,和银河旁边眨着眼的密密匝匝的星星,问奶奶:“喜鹊飞走了,谁给牛郎织女搭鹊桥呀?我们没有翅膀,又没多生出两条腿来,我们口渴了怎么办?”奶奶回答不了我的问题,后来,奶奶也变成了天上的一颗星星。现在,我庆幸自己在小城榆林居住,还能看到寥落的星辰和出水芙蓉般美丽的月亮,我庆幸铅色的雾霾还没有淹没我头顶的星空。 听听山泉水的声音吧!只要站在村头的老柳树下,哗啦啦的歌声就扑面而来。正对着村头的那条大石沟像是被闪电劈开的一条裂缝,一面石壁的上部呈悬空状,像一只振翅欲飞的苍鹰,山泉水就从鹰嘴里喷涌而出,形成一条瀑布倾泻下来。放羊的老汉蹲在鹰背上,吧嗒吧嗒地抽着烟,听着山泉水美妙的歌声,一辈子的愁肠事都随着那潺潺的泉水流去了,瞧,沟底的绵羊把天空里游动的白云都喝到肚子里去了!我们放学归来,山泉水和我们稚嫩的歌唱声形成山野里最甜美的合奏。傍晚,我们端着饭碗来到老柳树下,山泉水的弦歌为我们悠悠地伴奏。山泉水从远古走来,唱着永不疲倦的歌,给我们空旷的童年里装点了美妙的音乐。那是母亲喊我们回家吃饭的声音,那是乡亲们在黄土地上耕作时吼出的信天游,那是浩荡的西北风从黄土高坡刮过。 老井干枯的日子,乡亲们在石壁上凿出一条歪歪扭扭的小道去挑山泉水。泉水叮叮咚咚地敲打着水桶,溅起朵朵晶莹剔透的水花,赞叹声不绝于耳:“啊呀,这股好水!”奶奶的声音最响亮:“瞧这股水,清格湛湛的!”只是那道路又远又陡,等我们这些小孩子气喘如牛地挑回家,桶里的水已经所剩无几了。 然而,此时的老柳树下寂静如坟,只有蟋蟀焦躁不安的嘶鸣和墙根下几位留守老人搓牌的声音。我的目光开始变得焦灼,我循着石壁上残存的小路痕迹来到山泉水脚下,眼前的景象触目惊心:沟底乱石纵横,曾经被山泉水冲刷成一幅油画的石壁,风干成了伤心欲绝的泪痕,石沟张着干渴的嘴唇绝望地仰望苍穹。沟底有一眼井,那是村支书带领村民们掘地三尺挖出来的最后水源。 我疼痛的目光继续在故乡的土地上搜寻,村旁的水库早已销声匿迹,自从水库流干了最后一滴泪水,村里出生的孩子都成了旱鸭子。我寻找的足迹踏遍我们昔日放牛时的每一条深沟,然而,任是睁疼了眼睛,也看不到一滴水,我们曾经捉鱼戏水的小河哪去了?冒着一朵一朵小花的泉水哪去了?一位砍树的老大爷说:“别找了,现在的石沟里,渴死也找不到一滴水。” 我站在山圪梁上极目远眺,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被一片葱茏的绿色包裹,退耕还林政策使故乡的土地得以休养生息,野兔在山野里自由地奔跑,一些不知名的鸟儿也来这里安家落户,漫山遍野的绿意抚慰着我眼里的疼痛和忧伤。然而,听不到山泉水的歌声,远行的游子,将在哪里安放那份镌刻在心底的乡愁? 期待一场雪 北方的冬天,如果没有雪,就像青葱的年华里缺少了一场浪漫的爱情,北方的雪无需预约,它总会伴随着严寒的脚步姗姗而来。然而,今年冬天,雪似乎遗忘了北方的土地,时令已经过了冬至,天空里的云朵依然犹豫着,迟疑着。在道路上相遇的熟人,清清喉咙,舔舔干燥的嘴唇,微叹着互答着:“要是下一场雪就好了!”树木伸出枯瘦的手,等待着雪花丰腴它们的身姿,点亮它们的妆容。山峦瑟缩着皲裂的肌肤,等待雪花给它们披上盛装。 我在期待一场雪,因为雪天的那个故事一直温暖着我渺远的记忆。 去年冬天,新年的钟声即将敲响,我忽然心血来潮,要把我那一头永不驯服的羊羔毛般的自来卷发烫成柔顺飘逸的秀发。我哼着小调,迈着轻快的步子向理发店走去。天空中零星的雪花似乎也为我的奇思妙想兴奋不已,调皮地钻入我的脖颈,挠一下痒痒。 理发店里,一位帅气的小伙子热情洋溢地接待了我,看着他那稚气未脱的脸,我犹豫了:“你……能行吗?还是让你们老板来吧!”小伙子“啪”的拍一下胸脯说:“大姐,你就放心吧,做出来你就知道了!”接下来的一系列娴熟的动作让我彻底放了心,他拍拍我的肩膀说:“大姐,再等二十分钟就好了。”我静静地坐着,美好的期待就像无数洁白的雪花在脑海中轻盈地旋舞,我仿佛看到了朋友们见到我时瞬间闪亮的眼神,走上讲台时学生们“哇呜”的惊叹声,风和阳光在我的发间起舞,雪花轻轻坠落在我的发梢,倏然飘落…… “大姐,该洗发了。”小伙子说。当头发上的水分终于被吹干,站在我旁边的一个女孩子发出了一声尖叫,我的心猛然被拉紧了,急忙戴上眼镜,我的尖叫声让理发店里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我,我的头发就像一丛旺盛的沙蓬草,肆意扩张着它们的领地。我摸摸头发,早已僵硬而干枯。小伙子手里的吹风机停在了半空,局促不安地看着老板严峻的面孔。想起明天要开会,上课,参加同学聚会……想起许多眼神,嬉笑的,窃窃私语的,惋惜的……我终于按捺不住,一团怒火冲口而出:“头发做成这样,你让我明天怎么见人啊?!”他的脸憋得通红,嗫喏着说:“对不起……”老板的安慰,小伙子的道歉,都被我的愤怒远远地弹了回去,我铁青着脸夺门而去。 雪下得更大了,纷纷扬扬的雪花迷茫了我的双眼。这时我才想起由于一时气急,钱也忘记付了,“哼,谁让你做坏了我的头发!”我飞起一脚,将一团积雪踢得四散。多么怀念我那一头羊羔毛般的自来卷发啊! 夜晚,我辗转反侧,忽然想起自己打工的一段经历来。大二放寒假时,为了赚几个学费,我没有回家与父母团聚,在榆林的一家宾馆打工。早晨打扫卫生时,我端起一盆洗脸水就朝楼下泼去,就在那一瞬间我惊呆了,手里的脸盆“哐当”一声掉到了地上,楼下的一位中年男子落汤鸡似的仰起头,暴怒地盯着我,随即就像一股旋风顺着楼梯卷上来,冲着我挥舞着拳头咆哮,我的脸一定苍白极了,嘴里重复着:“我给你洗衣服……我给你洗……”这时,老板走过来了,我多么希望她能站在我面前,劝说一下青年也好,可是,她却背抄着双手,冷笑着摇晃着从我身边走过去了。就在我茫然无助之时,一对白发苍苍的老夫妇喘息着爬上楼梯,一边将他们的儿子拽下楼梯一边说:“走吧走吧,看把娃娃吓成甚了……”在以后的漫长岁月里,那一双苍老的面容犹如一枝跳动的烛火,为我抵挡着生命中的寒流。 也许,那个小伙子会受到老板的责备,会被扣掉工钱,甚至会被辞退……如果他的父母知道自己的孩子在外面受了委屈,溢满思念的脸上一定要泪水横流了。 第二天一大早,我匆匆走向理发店,推开门的一瞬,我看到了老板诧异的眼神。我把钱放在柜台上,对呆立在一边的小伙子说:“昨天太冲动了……”老板用颤抖的声音说:“大姐,让头发……再长两个月,我一定给你做得好好的。” 天放晴了!雪花在大地上铺上了洁白的信笺,等待人们抒写美丽的诗行。第一缕朝辉在雪地上涂抹出淡淡的红晕;一对恋人手挽着手走过,雪地上留下两行深深浅浅的爱情诗;路边,一个憨态可掬的雪人笑眯眯地看着来往的行人和车辆,那是孩子们用稚嫩的手写出的童话故事;树木就像进了大观园的刘姥姥一样,横三竖四地插了满头的花朵;另一家理发店的门口,两个小伙子将雪球互抛在对方的脸上身上,青春的激情随着雪花飞溅;小狗也来凑个趣,在雪地上踩几朵梅花……忽然觉得,我那沙蓬草似的头发在圣洁的天地里变得柔韧而美丽! 往事如洁白的雪花洒落在我的心灵深处,将我的灵魂洗涤得洁净无尘。我期待一场雪,虽然雪携带来的寒流像一条冷酷的鞭子抽打着北方的土地,但是,只要怀揣一颗善良的心,再冷的冬天,也会因爱而温暖倾城。 桃花依旧笑春风 那枝桃花无意中落入我的眼眸,是在懵懂无知的孩提时代。一本旧杂志里的一则故事深深地植入了我的心底:故事的主角是一对情窦初开的青年男女,一树绚烂的桃花涂抹出浪漫的背景,那脉脉含情的眼神,那欲说还休的神态,那离去时的怅然若失,那风,那蝶,那落花……此后,每年春天从花团锦簇的桃树下经过,那首诗就会脱口而出:“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那美丽的爱情故事也在平平仄仄中愈加清晰起来。 唐朝的那个春天,桃花笑得格外甜美。才子崔护独自去郊外踏青,也许是为了排遣落第的惆怅,也许是为了赏玩撩人的春光。途中,他轻叩那扇桃花掩映的柴扉,只是想讨一碗水喝,没想到开启了爱情的大门,一位艳若桃花的少女给他端来一碗水,倚着桃树静静地看着他,四目相对的一瞬间,仿佛一股电流穿透彼此的身体,风是怎么把花瓣抖落在少女发梢的,蝴蝶和蜜蜂是怎么亲吻花瓣的,两道目光是怎么纠缠在一起的,平静的心湖是怎么被风吹皱的,谁知道呢?他们只知道周身被浓郁的花香包裹着,像在飘渺的雾里,又像在朦胧的梦幻中。喝一碗水的时光有多长呢?仿佛过了一个世纪,又仿佛只是电光火石般的一秒钟。 转眼又到清明,春风染绿了柳枝又催开桃花,那个被桃花簇拥着的幽静院落就像一个巨大的磁场吸引着崔护,他再次迤逦而来,却只见柴门紧锁,阒无人迹,只有数枝桃花探出墙头,在春风中轻轻摇曳,似在翘首以待,又似幽幽地倾吐着万语千言。于是,他挥笔在柴门上写下那首流传千古的《题都城南庄》,怅然离去。崔护没有想到,一首不经意吟咏的诗竟然能在一个人的心中播下思念的种子,并且生根发芽,长成坚不可摧的大树,开出灼灼桃花。 真爱一定是能使人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也许是冥冥中听到了芳魂的召唤,也许是崔护的心中也激起了难以言说的微澜,牵肠挂肚的他再次拜访这户人家,用泣血的呼唤挽救了一个将死的灵魂,用赤诚的爱恋点燃了生命的火焰,有情人终成眷属。 沿着诗歌的河畔溯流而上,不难发现,描写桃花的诗词灿若星河,它开在《诗经》的源头:“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它开在陶渊明的桃花源里:“夹岸数百步,忽逢桃花林。”它开在杜甫草堂的篱前檐后:“桃花一簇开无主,可爱深红爱浅红?”……然而,它们在崔护的《题都城南庄》面前都黯然失色,那一抹生命的嫣红明明白白地告诉世人:真正的爱情根本不需要什么海誓山盟,门当户对,更不需要什么富邸豪宅,香车宝马,一个刻骨铭心的眼神就足够了。那氤氲的幽香荡涤着污浊的世风,那蓊蓊郁郁的桃林荫护着如露珠般晶莹,如雪花般纯洁的爱情。因此,那一树桃花虽历经千年的风雨,年年岁岁依旧在春风中洋溢着灿烂的笑容:“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贺昕 陕西神木人,高级教师,陕西省诗词学会会员,在《延河》等刊物发表散文多篇。 本篇文章来源于作者原创,版权均归作者本人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以上图片均来源于网络,如有版权问题请联系作者删除! 更多精彩敬请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hthaituna.com/htfzfs/11638.html
- 上一篇文章: 这种野花,大家都喜欢吃,若家乡有,请你看
- 下一篇文章: 踢上热搜的泾川聚力打造文旅康养靓丽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