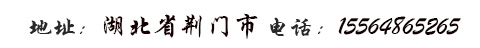青未了甜甜的红石榴
|
甜甜的红石榴 文|陈希瑞 在儿时的记忆里,在老屋的西间窗下,有一棵火红的石榴树。紧贴墙根儿,还有几棵金黄的向日葵。如果是盛夏,我常常在那里驻足,久久地观望,看着火红的石榴花和金黄的向日葵花交相辉映,爽心悦目,令人万分陶醉。 一到春天,石榴树那干枯的枝条开始微微泛青,探头探脑显出几片嫩叶。一场春雨一场暖,伴随着几场春雨的降临,叶子渐渐变得油亮,花苞在绿叶的陪衬下挂满枝头。正如“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一样,石榴花似乎在一夜之间红遍枝头。那火红的石榴花,一朵朵娇艳欲滴,蓬蓬勃勃,饱满而热情,任凭风雨的吹打,依然笑口常开。 石榴花开在时光里,岁岁年年,它们被文人墨客赋予了不同的思想内涵。 五月,正是石榴花开时,那一树的花朵红得耀眼,像西天飞来的一朵一朵的红霞。“翦碎红绡却作团。”白居易说,石榴花像剪碎的红绸簇成的团,这比喻真是生动形象。柔柔的,软软的,既温和又明艳,五月,因为有了它们的存在,显得愈发的清新明亮。“重五山村好,榴花忽已繁。”陆游眼中的石榴花,是闲适惬意的岁月静好。“微雨过,小荷翻,榴花开欲然。”苏轼笔下的石榴花,淡雅清新充满欢快明媚。 渐渐地,随着花儿的凋谢,随着那玛瑙似的小石榴一天天膨胀起来,火热的夏天如火如荼。韩愈有《榴花》一诗,赞得好:“五月榴花照眼明,枝间时见子初成。可怜此地无车马,颠倒青苔落绛英。”五月如火的榴花映入眼帘格外鲜明,枝叶间时时可以看到初结的小果。可惜此地没有达官贵人乘车马来欣赏,艳艳的榴花只好在苍苔上散落纷纷。 转眼到了秋天,小石榴眼看着变成大石榴,喜人的果实缀满了枝头。古人有诗云:“蝉啸秋云槐叶齐,石榴香老庭枝低。”秋高云淡,蝉声连绵。风吹茂密的槐叶,沙沙作响。石榴熟透,皮绽籽满,四处飘香,浓郁芬芳。累累的果实,压低了庭院中的树枝。 我们几个姐弟来到石榴树下,就像一群花喜鹊似的,叽叽喳喳,欣赏着,评判着。不知哪个调皮的,笑嘻嘻伸手托起一个大石榴,似乎要减轻一点石榴树的压力。不知哪个嘴馋的,张口提出要摘一个尝尝鲜。母亲颠着小脚,赶过来说,石榴树枝很结实,结再多的石榴,也不会压断。再说,石榴还不到火候,吃了会酸倒牙,不能摘! 直到深秋时节,满树的石榴,一个个展开了笑颜,笑得合不拢嘴。那一颗颗饱满的籽粒,在阳光的照射下,就像红宝石一样晶莹剔透,真让人满心地欢喜不尽。此时,父亲会踏着凳子,一个个小心地摘下来,递给树下的母亲或奶奶。我们几个姐弟一人一个,小心地一粒一粒送进嘴里,轻轻一咬,那甜滋滋的汁水,甜透了心窝! 看着我们吃着石榴,父亲说,看见了吗?石榴凝聚力很强,瞧瞧那籽粒,一颗颗密密匝匝,抱成团儿,才会形成一股甘甜的滋味儿。父亲看过一些闲书,其中就有《三国演义》,他说,古有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其实做人也是一样的道理啊!我们小小孩子,只顾享受嘴边的美味儿,哪管什么大道理?一旁的奶奶说,树大自然直,等孩子长大了,自然就会明白。母亲说,后街上马老六,三个儿子三房儿媳,死前没听说打仗闹火闹矛盾,死后更没听说为家产起纷争。居家过日子,和和美美就是好,过日子有劲头、有奔头…… 父亲和伯父,是爷爷奶奶膝下的两个爱子。听父亲说,上世纪五十年代,我们家三世同堂,伯父伯母在青岛谋生,一个学木匠,一个做小手工。父亲在县里工作,家里只有爷爷和母亲种庄稼。麦收季节,伯父伯母才从青岛赶回来,帮助麦收秋收,老老少少一大家人,为了过好日子,都很齐心。直到年春,为了支援边疆建设,伯父伯母远走新疆,来到地处伊犁河谷的伊宁市,从此天各一方。 直到年,从新疆回老家探亲、在老家长到十三岁的大姐说,上世纪五十年代,我母亲又要下地干活又要做饭,真是万般辛苦。母亲擀的豆面面条,做的苞米面饼子,大姐现在想起来还直流口水。做饭时,母亲双手捧着和好的苞米面,三拍打两团弄,椭圆形的饼子就成型了,然后,往煮地瓜的大锅边上一贴,再填几把草,拉一会儿风箱,饼子和地瓜的香味儿就开始扑鼻了。 大姐回忆说,春天,母亲带着她和妹妹(我大姐),去村边的地里种苞米,点种豆角。夏天,母亲从地里回来,挽起袖子就做饭,脊背塌湿了,薄薄的衣衫粘在脊背上,脸上的汗水,一滴滴落下来。秋天,奶奶抱着弟弟(我大哥),等着母亲从地里回来好喂奶。她和妹妹跑出老远去迎接母亲,为的是去抢母亲头上的苇笠,母亲的苇笠上,别着割豆子时捉到的大蚂蚱。等母亲烧火做饭时,把蚂蚱放进烧过的草木灰里,不一会就闻见香味儿了,赶紧扒拉出来,吹吹灰,姐妹俩这才一起享用。冬天的夜晚,母亲和奶奶煮一锅地瓜,地瓜烧暖了炕。第二天早晨锅边上热地瓜,锅中间放一个黑碗,装一碗水。母亲熥热了水,全家用它洗脸洗手,吃完地瓜,包着被子,坐在炕上,奶奶做针线,爷爷教大姐打算盘,希望她有个好出息。在大姐眼里,那时候,虽然日子过得清淡,但一大家人你敬我爱,相处融洽,温馨和睦,其乐融融。 大姐的记忆力真好,她回忆说,母亲晴天干地里的活,雨天和冬天做针线,还得抽空为我们洗洗刷刷,缝缝补补。寒冬腊月里,母亲脸上经常有冻疮,因为舍不得烧火,低矮的北屋十分阴冷,而母亲下午却来到南屋爷爷奶奶和她睡的那间,烧火煮地瓜做饭,饭做好了,炕也热了。 母亲有干不完的活,吃的却是最差的。爷爷有时候赶集买一块猪血,母亲熬一大锅萝卜丝子,猪血切成小块,放在菜盆边上,只有爷爷、奶奶和她才吃,母亲一口也不舍得吃进嘴里。年春夏,天旱的庄稼地都裂了口子,草根树叶吃光了,棉籽皮也没有了。爷爷从三爷爷家买了地瓜干,只给小孩吃;爷爷买回了烧酒糠,母亲把谷糠搅上地瓜面,攥成团子,给爷爷和小孩子吃,母亲舍不得丢掉洗酒糟的汤,把汤里加了一些野菜,和奶奶一块吃。结果,母亲和奶奶都中了毒,奶奶腰上长了个疖子,直往外流脓水,母亲脖子后和脸上,也长出了疖子,母亲用大蒜颠出汁子,往疖子上抹,结果,疖子没治好,脸色烧成了灰黑色…… 那时候,我们家北邻洪章大爷家,南面与陈光文爷爷家相邻,我们家的粉坊、场院都连着围子沟。大姐非常喜欢那围子沟,冬天折槐树枝上的螳螂籽烧着吃,春天采槐树叶和槐花充饥,采那墩茶叶树上的叶子,爷爷奶奶泡茶喝。最好玩的是夏天,雨后,捡拾淹死的知了猴烧着吃,采蘑菇蒸着吃,偶尔还能在树丛里,捡到几个鸡蛋,兴高采烈地拿回家交给奶奶。秋天,捡拾狗屎,划拉树叶子,准备冬天烧炕取暖,没听说谁家争争吵吵,谁家闹不愉快的事儿…… 所有这些一点一滴的往事,已经去世六载的母亲会记得吗?反正大姐记得,我也记得,每年采摘下来的石榴,除了自己享用,母亲还分给东屋西屋的大娘婶子们。他们感激地说,他婶子,你家孩子多,舍不得吃,还惦记着我们。母亲说,远亲不如近邻嘛,大家都尝尝。其实,人家也不是白吃我们家的石榴,隔些时日,人家会送来几根黄瓜、几个茄子或是一把大葱之类,以示谢意。母亲反倒是不好意思起来,同样说一些感激不尽的话。在我幼小的记忆里,母亲跟邻居相处融洽,从没跟谁吵过一次架,红过一次脸。 人与人将心比心,不管在外面、在家里,只要放正了心,心里才踏实,过日子才会一顺百顺,为人做事,要像石榴一样,才会结出甜蜜的果实,这是母亲在世时,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母亲不止一次地告诫我们,兄弟齐心,贵比黄金,一个家庭,只要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就没有过不好的日子。 构建和谐社会,是由千千万万个和谐家庭所组成。现实中,仍有一些嘈嘈杂杂不和谐的音符。过去的苦日子都熬过来了,现如今日子好过了,富裕了,人心反倒不干净了。君不见,有多少家庭,为了家产闹纷争,为了养老闹不和,为了钱财把脸翻。听说有的亲兄奶弟,因为家务事,竟然老死不相往来,不该啊不该...... 石榴如人,人如石榴。伴随着大姐的叙说,想起去世六载的母亲,仿佛一幅美丽动人的图画,映现眼前:高远的秋阳下,在老屋的西间窗下,那棵火红的石榴树上,结满压弯了枝头的红石榴,一个个憨态可掬的石榴们,咧嘴呲牙,憨憨地笑了,笑出了溢光流彩,笑出了柔情蜜意,笑出了甘甜芬芳…… 作者简介:陈希瑞,网名神仙哥哥,山东省青岛市作家协会理事,山东省平度市戏剧家协会副秘书长。作品散见于《大地文学》《火花》《青岛文学》《短篇小说》《辽河》《速读》《麦地》《悦读》《散文中国》《中国社区报》《山东工人报》《支部生活》《山东教育》《作家报》《齐鲁晚报》《半岛都市报》《农村大众》《青岛日报》《青岛财经日报》《老年生活报》《老年康乐报》《民主协商报》《大连晚报》《盐城晚报》《甘孜日报》《青海湖》《九天文学》《南方文艺》《西北文艺》《春晖文学》《北海文学》《天柱》《平度日报》《四平日报》《墨水古韵》《菲律宾商报》《有荷文学》《黄海散文》等海内外数十家报刊杂志和文学平台小说散文余篇,创作出34部吕剧、微电影和电影剧本等网络文学作品多万字,《亲亲的土地》荣获全国首届鄱阳湖文学“陶渊明”杯散文大赛优秀奖进入前二十名并被结集出版,多篇散文入选中国国土资源作家协会编辑出版作品专辑,古装吕剧《状元郎》搬上舞台。 壹点号胶东散文 新闻线索报料通道:应用市场下载“齐鲁壹点”APP,或搜索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hthaituna.com/htqxhj/12460.html
- 上一篇文章: 青未了红紫斗芳菲记家乡滨州的那片槐花
- 下一篇文章: 青未了母亲的身影,刻在春天的记忆里齐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