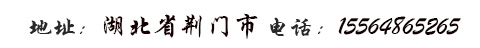王艳辉丨洋槐花国槐花
|
洋槐花 “抬眼一看,在流满了绿水的荷塘岸边,在高高低低的土山上面,就能看到成片的洋槐,满树繁花,闪着银光;花朵缀满高树枝头,开上去,开上去,一直开到高空,让我立刻想到在新疆天池上看到的白皑皑的万古雪峰。”没错,这段优美传神的文字出自季羡林老先生之笔,也是这段文字把我的思绪牵的很长,很长...... 童年、少年的记忆里,最常见的树木除了柳便是槐了。那会儿没有读过“杨柳依依”、“溪桥柳细”之类的词句,对柳不大在意,倒是槐更让我喜爱,因为每年春夏之交那缀满枝头的槐花,让我格外迷恋。 儿时,春风一起,我就开始盼槐花开了。槐花又香又美,还可以解馋。终于盼到了阳历五月,槐花开了,满村子飘起了淡淡的清香。大孩子、小孩子们便一圈圈围在了槐树下。大孩子爬上树摘了花往下丢,我们小孩子拽着衣襟在树下接着。等到我们的衣襟里兜不下了,大孩子们便纷纷从树上跳下来,我们就找个阴凉处坐下来一起享用这自然的馈赠。记忆里有个稍大的男孩,家里孩子多,总是吃不饱,他便用槐花充饥。脑子里清晰记着他撸一把槐花也不去蒂,大口大口往嘴里塞的情景。而并无饥饿的我只是贪恋槐花那一丝甜。我把花瓣一瓣瓣扯掉,只剩一根顶着花蕊的花柱,我只吃那花柱。有时也会掐断花托,吸食子房里的花蜜。我这种吃法还曾招来同伴菊的奚落:“看看,就数她秀迷。”后又转过身指着我:“你是大小姐吗?”同伴荣听后就白她一眼:“你管人家咋吃呢。”每每这时,我就感激地唤一声“荣姐”。 我盼着槐花开还因一桩隐秘的心事,每到槐花开的季节村里便来放蜂的。他们在村外的场地上搭起帐篷,摆好蜂箱。放蜂的女人很年轻,细眉细眼,皮肤白皙。头上包着一块红纱巾,夕阳的余辉中她弓身在蜂箱旁忙碌,头上的红纱巾比霞光更艳。我常常站在不远处静静看那女子干活。村西的小脚三奶奶笑呵呵地对我说;“丫头,馋蜂蜜了吧,让你妈给你买来呀。”我笑而不答,我才不告诉她我是喜欢那个放蜂的大姐姐呢。 槐花就这样牢牢占据了我的记忆。而且我的认知里,槐树就只这一种,直到读了季羡林老先生的《槐花》,我才知道盘踞在记忆深处的槐花是洋槐花。而与国槐花的迎面相遇则是多年后的一个夏末了。那时我在省会读大学,一个夏日周末跟同学出去玩。见路旁的大树上覆着一层米色的小花,单个花不大,聚在一起,就成了气候,远远望去,似层层叠叠的云,开在半空中,倒颇有几分气宇轩昂的样子。我问同学:“这是啥花?”同学答:“国槐花啊。”哦,恍然中,我仰头看向那国槐花,花型很小,不大起眼,也不香,细细闻来,似乎还有一点腥气。彼时已是夏末,我很诧异此花何以选择这样一个季节开放。顶着夏季的暑热开了,被太阳火辣辣地炙烤着,而等在前面的是秋的萧瑟。何况它没有洋槐花的洁白清雅,也没有洋槐花的醉人芬芳。那一年,我正值桃李年华,行走在人生之春。 虽然也曾抱怨过时间是个老贼,默默偷走一切。同时也深深感恩时间赐予的思考与智慧。大约是中年以后的人生之秋里,我对洋槐花与国槐花有了新的认知。倘若做人,我更愿做国槐花那一种。我不愿如洋槐花那般绽放在百媚千红争奇斗艳的季节里,香气袭人,一开始就站在高处,占尽先机、看尽风光。我更愿如国槐花一般开在季夏的骄阳里,不艳、不争,隐者一般,淡淡地开,薄薄地颤。 近日,重温《红楼梦》,掌管荣国府的王熙凤,出身于王侯贵胄之家,又生的美艳异常,“身量苗条,体格风骚”,恍若神仙妃子,手握荣府大权,可谓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可她机关算尽后,反落个众叛亲离、惨死狱中的结局。而红楼里的另一个女子——邢岫烟,家道贫寒,投奔邢夫人、寄居紫菱洲,她温厚平和,安贫乐业,宝玉曾盛赞她“超然如闲云野鹤”,这样一个贫寒女子最终嫁给了儒雅俊秀、沉稳务实的富二代薛蝌。成为红楼梦里结局最好的女子之一。 我想,人生的开场大抵有两种。一种是洋槐花般晴空丽日里开始就站在高处,端的是看尽无限风光,另一种是如国槐花一般,人生之初是山谷浓荫里一条涓涓清瘦的细流,它缓缓流淌在蜿蜒山岭中,但它不躁、不急,笃定前行,最终,抵达了远方,生命呈现出一种磅礴开阔的气象。彼时,当无怨,也无憾。 国槐花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hthaituna.com/htwxtz/11716.html
- 上一篇文章: 精准让贫困村土里生金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