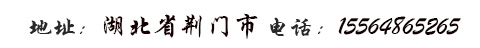故乡的树冯美莲
|
北京白癜风治疗的价格高吗 https://wapjbk.39.net/yiyuanzaixian/bjzkbdfyy/ 故乡的树 ◇冯美莲 走在城市的人行道上,蓦地一缕花香扑入鼻内,然后,又是一缕、两缕……我知道这是桂花的香味。上师范的时候,我喜欢用那种两元钱一小瓶的廉价桂花香水,就是那个味儿。真好闻! “桂花树不是南方的树么?怎么到了我们这个北方小城?” “现在城市都在搞绿化,不管是大城,还是小县,许多南方树被运来作绿化树、行道树。包括桂花树。这些树价格不便宜呢!”夫说。 “咱们本地不是有很多树种吗?桐树、柳树、杨树、榆树、槐树、椿树(此处指臭椿)、楝树,而且绿化起来肯定成本儿低呀!”我生气了。 “可能南方的树不招虫吧。”夫揣测道。 “不招虫,不招虫,”我喃喃道,思绪却回到了儿时…… 老家是鲁西南的一个小村庄,那时家家户户都有宽敞的院子,当然全是裸露着土壤的,院墙外、村里的街道更是土泥地的。院里院外栽的不外乎这些树——椿树、楝树、榆树、槐树、枣树、杨树、桐树,一户院子里有五、六种,七、八种高大的树一点儿都不稀罕。那时的人们喜欢树么。 这些,是故乡的树的代表。 一进胡同,就瞅见了我家门口的那棵臭椿树(我家的门儿是几根木头、棍子订成的柴门)。说是臭椿,我却没闻到过臭味儿。为什么这样叫它,想不明白。树很粗了,它枝上挂的那是花儿呀,还是种子呀,不知道,反正很好看,像少数民族女子额前戴的一排银饰,只不过不是银色的,是那种浅绿,绿中又泛点黄色。家乡人称它“椿牌儿”(取音似)。最关键的是它树上常趴着一种昆虫:身上有长长的翅膀,翅膀上布有黑色的斑点,它一飞起来,就露出翅下的眩目的大红底子。这虫子是我们小孩子的玩意儿,它学名叫什么,同样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大人们都叫它“椿蹦蹦”,可能是因为它会蹦吧。你看,树身上趴了很多“椿蹦蹦”,我们蹑手蹑脚过去,手心蓬起成网状,猛地向它罩去,但它已先你一步蹦开了。小孩子们可不干了——难不成还逮不到你?继续追,它蹦一步我们撵一步。结果当然逮不着的时候居多,但我们乐此不疲,这其中且有无限的乐趣在呢!你听: “唉!又蹦走啦!” “看这回,我不抓住你。” “抓住啦!抓住啦!” “叫你再蹦,你不能啦!” “老三(大大爷家的三闺女),你抓几个?” “俩。” “我咧仨,你没我咧多。” 正对着椿树的东面,是一棵楝树。也有年头了。它的叶子很好看,秀秀气气的。花也很好看,紫色的,星星点点,对,就像紫色的星星,或浮于叶面,或藏于叶间,羞羞答答,朴素而又美丽。可谁又能想到,这样一个秀秀气气、羞羞答答的可爱女,竟是勤劳的、多产的,看——花去果来,树上结了很多楝楝豆,一圪垯一圪垯的,圆乎乎的。等长到和琉璃蛋儿大小差不多时,我们就把它们够下来玩儿。玩儿法和和琉璃蛋儿差不多,可那时哪有闲钱买那贵东西。现在回想起来,我真佩服那时的人——大人、小孩儿。贫穷并没有让他(她)们的生活失去欢乐,他(她)们反倒就地取材,打下楝楝豆,在地上挖一个比楝楝豆稍大些的小圆坑,以圆坑为中心,在四周用棍子画一个正方形,在其中的一个边上,两头留相同的长度,剩下的线段为宽,向外延伸再画一个长方形,这个长方形通常要有一两步长。最外面那个线(长方形的宽)就是起点,周围的框儿类似于边界线。游戏开始,大家争着把对方的子儿弹出界外,好扫除障碍,第一个把自己的子儿弹进圆坑内。写到这儿,我怎么觉得我们以前玩的这个游戏和现在的“冰壶”差不多呢!真是的,想想我们三十多年前就玩儿“冰壶”这样高端、大气、上档次的运动,美气得很——这可是奥运会的正规比赛项目呢!当然,小时玩儿的时候可没想到什么“冰壶,”我们嘴里念叨的是这(取音似):一骨碌弹,二骨碌黏,三小吊儿,四小庙儿。在喃喃自语中,楝楝豆进了小圆坑——赢了。原来,这个小圆坑就是小庙儿。 这个游戏占据了儿时将近一半的时光。那时,不论男孩子、女孩子都可以玩这个(我就是个女孩子吗)。玩到天落黑才回家,灯泡下一照,手指甲盖儿里都是泥。 院子中间是一个压水井,它的旁边长了几棵高大的榆树和洋槐树。春天里,榆钱儿先开了,一嘟噜,一嘟噜,肥肥的,像婴儿胖嘟嘟的小脸儿。娘用镰刀绑在长棍子上够下来,给我们搋榆钱儿馍吃。再往后,不知哪一天,一丝花香神秘地飘过来,得使劲吸才能过瘾,哦,是槐花开了呢。抬头,一枝,或者两枝槐花正咧着嘴儿偷偷对你笑呢!什么时候开的?也不给说一声,心里小声咕哝道。槐花听了,也不生气,依旧咧着嘴儿笑。又过了一天、两三天罢,看,满树,一树又一树,一家又一户,雪白雪白的花朵像商量好了似的,一齐露出皓齿,笑得花枝乱颤,笑得香气飘到四、五里地外。小孩子们把刚摘下来的槐花用手一捋,捋一大把,塞进嘴里,香气中带着丝丝甜气,好嚼,又不留一点儿渣滓。不停地捋,不停地塞,以致牙缝儿里都冒着甜气。大人们则喜欢蒸槐花,或煎槐花汆汤喝。 喜欢它们,不只是因为它们的香气,它们能吃(那个年代,吃榆钱儿、槐花是因为个穷;现在吃,好像是一种习俗。有一年我曾对夫说:唉!今年又没吃上榆钱儿),假如它们没有香气,不能吃,我也喜欢。只因为,它们是故乡的树。 一次去济南,无意中拐进了“槐荫区”,还真是和区名一样,路两旁是成行的槐树(黑槐)。时值夏天,树叶深绿,那绿浓得好像用开水也化不开。从周朝起,宫廷之中就开始种植黑槐,因此,黑槐也叫国槐(与前面的洋槐不一样)。听说北京故宫有十八槐古迹,北京市街头巷尾和郊外的一些村庄也留存了不少参天古槐,幸甚至哉! 楝树的北面不远处有两棵枣树,一棵是菱子枣,一棵是老糠枣。惊蛰一过,其它树木都殷勤地发芽、抽叶、开花,枣树却没有动静——干点儿事儿为啥都要凑堆儿呢?它有它的打算哩! 春去夏来,光秃秃的枣树上拱出了鹅黄的芽,像鸟嘴儿。几场淅淅沥沥的小雨过后,芽舒展为叶,鹅黄氤氲为浅绿,点缀着褐色的枝干。这时候的枣树别有一番韵味,如一幅小水墨画。 “麦黄杏,”杏子都黄了,枣树才开花,却开得密密匝匝,开得甜气四溢,开得蜜蜂嗡嗡叫(堂哥养了十几箱子蜜蜂,这下可有活儿干了)。那枣花黄中透着绿,绿中洇着黄,仿佛小米粒,一簇一簇簇拥在枣叶间。枣花是禁不得有动静的,“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簌簌衣巾落枣花,”一场雨,一阵风,下面就是一地的枣花。偏偏家里养的鸡又爱在枣树上过夜(菱子枣树不高,枝枝杈杈却很多,鸡很容易就能飞上去),怕黄鼠狼么。天一落黑,鸡们便蹲在低矮的土墙上,扑棱棱、扑棱棱飞到枣树上,找个地方卧下来。枣花又落一些。终于等到花落完了,结果子了,小枣在哪儿呢?瞪大眼睛仔细瞅:一个个像绿色的针尖儿,缀满枝头。这时候的枣树又像是一幅摇曳的明丽的水彩画。 “针尖儿”慢慢地长大,像变魔术似的,成为拇指肚儿大小的青枣。总是有那么一天,望着青枣:摘个尝尝呗,看好吃不。枣枝被压得很低,踮起脚尖儿,伸手,拣一个个儿大的,放进嘴里——既不涩,也不甜,平平淡淡,不好吃。还不到时候吗! 当街有一大片空地,上面种了两棵石榴树和七八颗枣树。这是四老兰(一个小脚老太)家的地和树。夏夜,大人在繁茂的枣林下纳凉,小孩子则在人群中窜来窜去,玩“藏老摸儿。”不知谁家的臭小子爬到枣树上,站在上面往下撒尿,引得大人们一阵呵斥:“这个小熊孩儿……” 立秋了,枣儿又长大许多,青色中泛出了白色。娘说,枣儿一白倍儿,就有甜味儿了。孩子们忙着上学,大人们忙着去庄稼地里干活儿,谁也不晓得枣子何时又变成了红色。先是红了向阳那一面,接着整棵枣树都红了。总有几个绿的犯倔,就是不变红,那又有什么关系呢——绿的这时候也甜掉个牙。红色映衬着还且绿的浓密的叶,绿叶烘托着红玛瑙般拥挤的果。这时的枣树极像一幅泼墨画,你只管大胆地泼。 八叔(其实是四叔)家门外有一棵枣树,结的是老婆儿枣儿,非常甜,样子也很特别,像今天的马奶子葡萄,只不过要比马奶子葡萄大很多。这棵枣树身材修长,像杨树一样,太高了。我们小孩子经常捡起砖头、瓦片、土坷垃,朝树尖儿上最红的那个扔去。“咚”、“咚”、“咚,”最中意的那个红枣儿没掉,其它枣儿掉了一地,枣叶子也掉一地。正撅着腚拾枣儿,一个高个子的小脚老太太“笃”、“笃”、“笃”地捣着拐棍儿从院子里出来了:“又够枣儿咧,又够枣儿咧,你看看,把绿咧都够掉啦,回恁家够去。”说着扬起了手中的拐棍儿。我们顾不得没捡完的枣儿,一哄地跑了。她是我奶奶,跟八叔过。吃她个枣儿都不愿意呢! 这里不叫吃,换个地方(其实,谁家都有枣树,都不缺枣吃,小孩子淘气,不是图个玩儿吗),去枣树林。四老兰坐在一块石头上,正在看护枣儿。我们就玩起了游击战,打一处换一个地方,那老婆婆,哪儿跑得过几个淘气娃呢,又是小脚儿,最后只能坐在地上喘粗气,她跑不动了。我们也见好就收,猫到某个角落比自己的“战利品”。 深秋了,寒露节气快到了,家家户户开始打枣儿。把枣树下面的地用大扫帚扫干净,铺上塑料布、床单子。娘和哥拿着长杆子,“嘭”、“嘭”、“嘭”敲打着树枝,我和姐在下面拾。不时有枣儿“咚”一声砸在头上,脊梁上。要在平时,我早就撂挑子不干啦,可眼下,谁顾得上这——嘴里塞得满满地,大红的枣儿可不要都叫姐给拾走了。为了犒劳我们,娘红的绿的煮了半锅枣儿。煮好的枣儿又糯又甜,煮枣儿的水上浮着一层白沫儿,枣儿上也沾着一层白沫儿。红得特别好的枣儿被切成片儿晒。家里那棵老糠枣,光听名就知道不好吃,它个大,成熟得很晚,要等到快下雪了才可以摘下来,一般用它囫囵个来晒干枣。“七月十五枣儿红圈儿,八月十五晒半干儿,”看,场上晒的红彤彤的就是枣。这儿一片,那一片,好几家的呢。枣儿晒好放起来,等到过年,家家户户蒸豆馅儿馍(干枣片儿是主角,还有红薯干,红小豆)、枣儿花(馍设计不同的造型,上面嵌入一个或几个泡好的囫囵的干枣儿),人人一顿能吃上一、两个呢。 忘不了杨树。小村庄紧挨着国道,国道两旁是两行齐刷刷的杨树,一直向南、向北延伸,像一列看不到头尾的火车。它们会一直向南北延伸到哪儿呢?这些树真高,仿佛要蹿到云霄里去。有些树,一个大人都搂不过来呢。夏天的时候,我们可享福了,走在公路上一点儿都不热。 遇到刮大风、下大雨的天气,许多杨树枝会被刮折,等到风停了,雨可能还没住,娘忙叫上哥,去公路上拾树枝——去晚了就被别人拉走了。粗的树枝娘拉着都吃力呢。哥对娘说:等俺妹妹长大,咱也抬个更大的。两个人满载而归,这下羊圈里的羊可撒欢儿了,它们扯着、嚼着杨树叶,还不时地抽空抬起头,温情地瞅上你一眼,冲你“咩咩”叫上两声,好像对这顿饕餮非常满意。 我有许多的时光从杨树的身旁经过。未上学时,秋天,天已转凉,我穿着凉拖鞋,拿着系着长绳的竹签子(大人用筷子削的),去扎这些杨树落下的枯叶。扎满绳子,拉回家,放到厨屋里烧锅用——娘看见了肯定会夸我的;初中三年,天还未亮,就要去早读,骑车上国道,直走三四里,学校就在路东边。一路相伴的除了几个堂姐、堂妹,还有那杨树。中午放学,四五个毛丫头叽叽喳喳,骑着车子还不忘呱啦呱啦班里的新鲜事,杨树只管听,也不发表意见。晚上放晚自习,也许月明星稀,也许黑夜如漆,杨树瞪大着眼睛,婆娑着树叶,护送着我们;放假过年,几个丫头片子结伴去会上买小妮子喜欢的东西,手绢啦,纱巾啦,搓脸油啦,皮筋儿啦,路上丢下一串串笑声,杨树仿佛也在说好看着呢;最忘不了,冬天,帮娘推一架子车的大白菜去会上卖(会逢四、逢九,地点就在我们学校边的国道两旁)。这架子车装得真满,前头、后头都套着荆笆,后头套荆笆一是防止白菜滚掉,二来也能多摞一层白菜;前头,唉,你要是现在看见,肯定大吃一惊——荆笆都套到架子车的两个辕上了!这不超载了么,怎拉得动呢?从家上国道也就二百米,棘手的是有一百米的土坡,坡度还不小呢。要是没有我和姐(爸在县里上班,哥跟着爸上高中)在后面使劲推,娘肯定上不了坡。走时黑乎乎的,拉到地方天已将明。几百斤的白菜啊!两旁的杨树知道,娘汗流满面,里边的衣裳早已溻透了。 “家有梧桐树,引得凤凰来,”“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更妙的是苏轼的“缺月挂梧桐,漏断人初静”。从先秦开始,历代文人骚客将梧桐咏入笔端。我的故乡也有桐树,可大人说,那叫泡桐。上网查查,中国泡桐网上说:“关于泡桐的名称,古代传说很多,直至今日,我国大部分地区的群众仍称泡桐树为‘梧桐树’、‘桐树’,有的地区称之为‘凤凰木’。”所以谁又敢下妄言,说古诗词里没有泡桐的身影? 桐树院子里栽,地里种得更多。地头儿,地尾儿,两家的地边子上。清明前后,桐树开花儿了。你见过满树的花儿吗?它的叶子好像没有几片,只看见花儿。花开得一朵挨一朵,你挤我,我挤你,层层叠加,一枝上就有十几朵抑或几十朵,千朵万朵却不曾压枝低。它们一个个像金钟,像喇叭,不过这金钟和喇叭都是淡紫色的。远望去,一树的紫色,一树的梦幻。桐花的香,怎么说呢?清气中挟着少许妩媚,可爱得刚刚好。夜里起风了,下雨了,第二天早晨,桐树下一地紫色的喇叭。我们小孩子笑着、跳着去拾那些喇叭,放到嘴边“嘀嘀哇”“嘀嘀哇”吹起来。立夏将至,开了二十来天的桐花悠悠飘落,完成了它的使命。这时,叶子才正式登场,开始长大,长大后的叶子可是真大,像一把把蒲扇。夏去秋来,,桐树上冒出了许许多多棕色的东西,像一个个秦朝的箭镞,高抬着头,意气风发(桐花谢了之后就有这些东西,只是以前没注意)。这些是桐树的花苞,来年是要开桐花的。朔风吹过,桐叶却不曾变黄,仍一片一片绿意,这绿意会一直延续到小雪节气。对了,它是有果实的,椭圆形,像棉铃桃般大小,青绿色,后来,慢慢慢慢变成了褐色、黑色。掰开来,却是四个小房间,里面藏着它的种子呢。种子轻飘飘的,几乎没有重量,又太小、太多了,把它们倒出来,如一个个极袖珍的白蝴蝶,躺在手心里,煞是惹人怜。 与学校后操场隔墙的人家,有一棵繁茂的桐树,每天我在三楼讲课,一扭脸,就能看到它。偶然的,上课时提到了桐树。我问学生见过桐树吗,满座寂然。正伤心失望时,一男生举起了手,且“嗤嗤”地笑着:“老师,我见过,”他用手指了指,“咱后面操场的东围墙外,那一棵树枝都伸到咱学校的树就是桐树,”他又“嗤嗤”地笑了,“我从小对桐树的花过敏,所以我知道桐树。”我不禁讶然了,幸好还有人认识它——但理由又多么令人瞠目结舌呀! 桐木可制良琴,“斫而为琴,弦而鼓之,金声而玉应,”贫穷年代亦可为女儿打嫁妆;桐油可制油纸伞,“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桐树可抒情,抒高尚之情、寂寞之情、惆怅之情,“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正苦。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 “凤凰非梧桐不栖,”但我们不再有时间、有时间也不去理会传说;我们有了钢的琴;有了不刷油的绸的自动伞;有了高档家具;盖房子有了钢筋、水泥;有了冗长冗长的垃圾剧;有了咖啡厅;有了灯红酒绿。你们被利用完了,没有价值了,所以要被丢掉——过河拆桥? 从师范毕业全家搬到县城,已二十年不回故乡了。如今重回故乡,是深秋,田野收割殆尽,冬小麦已出土。远望去,平原一览无余,几棵孤零零的树可怜怜地站在那里,再没有了昔日前呼后拥的辉煌。枣树林子早已杳无踪迹,上面也没有盖屋,那么大一片地方,荒草萋萋,穿插着几条任由众人踩成的横七竖八的干硬的路。枣林的主人——四老兰婆婆早已驾鹤西去,她活了一百多岁,听娘说这婆婆最后都糊涂了,啥都不知道了。我那活到九十三岁的奶奶也作古十来年了。我上初中的那几年里,她经常怀里偷偷地揣着一、两块月饼或几个苹果,拣没人的时候,颤颤巍巍地走到我家院门口,叫我和姐拿走。我俩若是不要,她会气鼓鼓地又用拐棍儿使劲儿捣着地皮,她是在想弥补以前的不好呢。早在十多年前,国道重修,两边的大杨树被伐掉,一棵都不剩,取而代之的是几棵小杨树、小柳树,稀稀拉拉、又黄又瘦。在农村,村里的街面被硬化,庭院也被硬化,或许在水泥地四周的罅隙里(一般指墙根处)留有少许的土壤,却种上了桃树、柿子树,架起了豆角儿、黄瓜、丝瓜,栽上了韭菜,撒上了生菜、小油菜。 没有了那些高大的树木,我们的生活便不再拥有仰望。 置身新建的几处公园,满眼都是叫不上名字的陌生的树。我看不到故乡的树。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哦!今晚的月亮还是故乡那轮月亮么?今晚的月光还是故乡那时的月光么?若是,还能把故乡的树照亮么? 我的故乡的树! 岭南文苑 冯美莲,山东省东明县第二初级中学教师,从教语文二十余年。布衣暖,菜根香,诗书滋味长……唯愿人生过得简单且从容。 免责声明: 作者授权“岭南文苑”公开发布, 文章内容不代表平台任何观点! 制作:王利军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hthaituna.com/htbhjb/11900.html
- 上一篇文章: 故乡散忆39一种美味胜过荠菜的野菜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